 1、 学科认同和定位 之所以要在这个场合说“学科认同和定位”,是因为昨天两位讲者给我的强烈印象之一是,他们很清楚“我是谁”,因为他们各自对自己的学科认同和定位有清晰的概念。遗憾的说,这不是国内民族音乐学学界的状态。学科的认同危机,其后果便是无从无所,失去自我。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与黎、王教授和在场的各位交流我对我们民族音乐学学科认同和定位的小见。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实质是希望通过解析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以及“思想~行为”直接的互动关系来获得对人类文化??甚至是“人”的宏观认知。由于研究领域、对象属性、或研究指向不同,不同的学科在“思想”和“行为”这条连续线上有不同的切入点。 “音乐学”属性的“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是研究人类文化中有关音乐“思想”和“行为”的学科,它想解决的问题是“音乐是什么?”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音乐作为制成品的内在结构、音乐的制作过程和音乐是如何给接收的这三个互相关联的互动层面;前两个层面是“行为”,后一个层面是“思想”。 目前一般所指的“民族音乐学”,是北美体系的“民族音乐学”,是学科中的一个方面,不是学科的全部。北美发展的“民族音乐学”,大致有“把音乐置于其文化环境中来研究”(“to study music in its cultural context”)(Hood 1971, 1982)和“把音乐作为文化来研究”(“to study music as culture”)(Merriam 1964)两个取向。前者给人归类于具“音乐学”视野的民族音乐学(这其实是对“音乐学”的误解);后者则被视为具“人类学”视野的民族音乐学(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 音乐作为制成品和过程(制作和接收),在具“人类学”视野的民族音乐学学者们的口中便成为“音乐本体、行为、概念”(music sound ? behavior about music ? conceptualization)(Merriam 1964: 32 ? 35 ),我们可以看出,这仍是在“思想”和“行为”的框架内在打转。 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思想~行为”上的差距,也即“局外”“局内”的问题,不但是民族音乐学,也是所有社会人文学科所面对的挑战。为此,北美民族音乐学除了实地考察,并有提出通过对被研究者的音乐演奏的学习,培养“双重音乐感”(bi-musicality,1960),以取得对其的“近”经验共鸣和认知。
1、 学科认同和定位 之所以要在这个场合说“学科认同和定位”,是因为昨天两位讲者给我的强烈印象之一是,他们很清楚“我是谁”,因为他们各自对自己的学科认同和定位有清晰的概念。遗憾的说,这不是国内民族音乐学学界的状态。学科的认同危机,其后果便是无从无所,失去自我。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与黎、王教授和在场的各位交流我对我们民族音乐学学科认同和定位的小见。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实质是希望通过解析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以及“思想~行为”直接的互动关系来获得对人类文化??甚至是“人”的宏观认知。由于研究领域、对象属性、或研究指向不同,不同的学科在“思想”和“行为”这条连续线上有不同的切入点。 “音乐学”属性的“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是研究人类文化中有关音乐“思想”和“行为”的学科,它想解决的问题是“音乐是什么?”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音乐作为制成品的内在结构、音乐的制作过程和音乐是如何给接收的这三个互相关联的互动层面;前两个层面是“行为”,后一个层面是“思想”。 目前一般所指的“民族音乐学”,是北美体系的“民族音乐学”,是学科中的一个方面,不是学科的全部。北美发展的“民族音乐学”,大致有“把音乐置于其文化环境中来研究”(“to study music in its cultural context”)(Hood 1971, 1982)和“把音乐作为文化来研究”(“to study music as culture”)(Merriam 1964)两个取向。前者给人归类于具“音乐学”视野的民族音乐学(这其实是对“音乐学”的误解);后者则被视为具“人类学”视野的民族音乐学(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 音乐作为制成品和过程(制作和接收),在具“人类学”视野的民族音乐学学者们的口中便成为“音乐本体、行为、概念”(music sound ? behavior about music ? conceptualization)(Merriam 1964: 32 ? 35 ),我们可以看出,这仍是在“思想”和“行为”的框架内在打转。 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思想~行为”上的差距,也即“局外”“局内”的问题,不但是民族音乐学,也是所有社会人文学科所面对的挑战。为此,北美民族音乐学除了实地考察,并有提出通过对被研究者的音乐演奏的学习,培养“双重音乐感”(bi-musicality,1960),以取得对其的“近”经验共鸣和认知。 
 那么怎样让学生也具有这种反省的水平呢?是不是一定要有留学的经历后才能有自我反省的能力?所谓他者的眼光,一定要经过他者的眼光、经验才能在我们自己的本土看这个差别,这样才能一清二楚,如果你没有进入他者就很明白自身(所谓西方学界的批判精神不也是由此而来的吗?)所以我一定不会做“翻译”的工作、不做传声筒。 第二个体会是就是“时间”问题,用nature time等等,我的感受是,从第一个层面可能是所谓的logical time ,我学到的是哲学家谈的有限与无限。有限时间在仪式研究中是无限的,而且有限的空间在仪式中也完全改变,比如道士,他们所学的就是怎样把凡俗的东西转变成脱俗的东西。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不知道仪式研究的学者会不会培养自己的宗教感情,走到宗教氛围中去感受神圣的世界,宗教学学者是有这样的体验行为的。仪式研究也是时间、空间的建构,因此我们的工作是相同的,就是在仪式中如何来看人类世界。 王铭铭:我想说,听了刚才两位老师的发言,特
那么怎样让学生也具有这种反省的水平呢?是不是一定要有留学的经历后才能有自我反省的能力?所谓他者的眼光,一定要经过他者的眼光、经验才能在我们自己的本土看这个差别,这样才能一清二楚,如果你没有进入他者就很明白自身(所谓西方学界的批判精神不也是由此而来的吗?)所以我一定不会做“翻译”的工作、不做传声筒。 第二个体会是就是“时间”问题,用nature time等等,我的感受是,从第一个层面可能是所谓的logical time ,我学到的是哲学家谈的有限与无限。有限时间在仪式研究中是无限的,而且有限的空间在仪式中也完全改变,比如道士,他们所学的就是怎样把凡俗的东西转变成脱俗的东西。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不知道仪式研究的学者会不会培养自己的宗教感情,走到宗教氛围中去感受神圣的世界,宗教学学者是有这样的体验行为的。仪式研究也是时间、空间的建构,因此我们的工作是相同的,就是在仪式中如何来看人类世界。 王铭铭:我想说,听了刚才两位老师的发言,特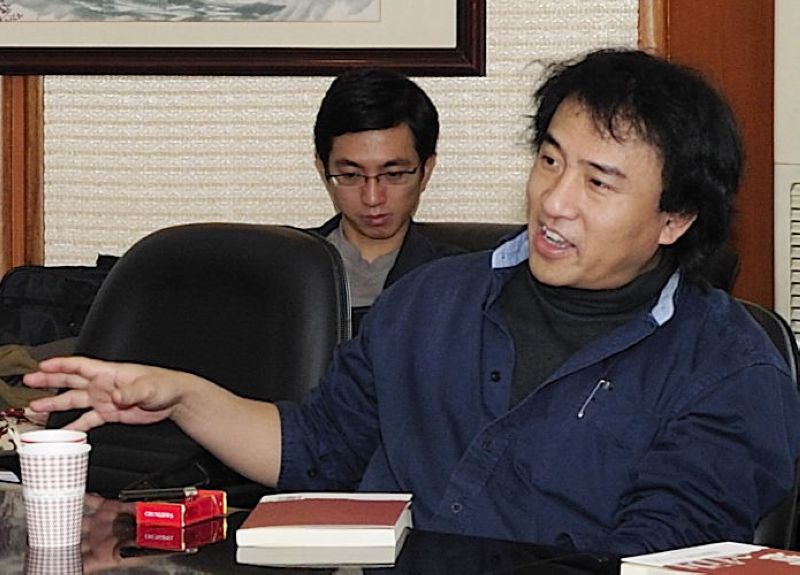 说到人类学学科本土化的过程,人类学这门学科的本土化或建立中国自己的叙述是在1920-30年代这个阶段,最早在吴文藻的身上出现这样的感受,当时在美国的留学学刊上发表《民族与国家》,把世界各国的理论都做了批判,后回来燕京大学,当时就提出了用中国话来讲社会学,刚才说到像中文大学,我听说那里必须用英文或广东话讲,像我这样英文不好、广东话又不会讲的人,到那边和人家交流得时候就会失败。我们早就说社会学要中国化,那么中国化是什么意思呢?(吴文藻)他用中国的语言来讲、用中国的文字来写,并没有像前面所说的学理层面上的,我们中国的社会情况用nation 和states合在一起,然后提出一种叫society这个概念。而只是说用“中国话”来讲就很重要,今天回去看,他有点太简单,但简单里面却含有很深奥的东西,就是说我们社会学里面有没有“中国话”?或者在音乐学里面,即使你用汉语讲,你仍然不见得就是“中国话”。我之所以说大家很幸运,是因为我们在探讨这样一种语言,吴文藻当年以为自然而然的用中文讲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像严复甚至林?那样用文言式的中国话翻译西学,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每个人讲的话都有点像英语式的那种句法,连法语都不大像。务实的说,想寻找一种语言(明白精义)就要寻找一种关键词、关键概念,就是可能带有讲话人的那种本质思想的特制的语言。这里我并不是像汉族中心主义那样要排斥少数民族或者农民的语言,而是说我们汉语学者要清楚,我们的“关键词”是哪一些,最后能够达到跟我们的研究对象的交流。 我们到底用哪些关键词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我最近正在探讨我们关于“人”和“物”的概念,这是最基本的。涂尔干说我们研究社会学方法的最基本原则是要把社会看做一个thing,我们说研究人也好、研究声音也好,可能声音是个“interview”,但是如果你没有把他看成是一个thing, 而且这个thing是跟人不分开的,那么你可能很难领会这个nothing的意思。 其实中国古人对“人”和“物”的关系、内容有很多深入的讨论。我明天到上海大学讲“人物”,西语把人叫person等等,它很明显没有把“物”的意思放进去。但我们说一个人叫“人物”,是person thing??这其实能使我们解开社会科学的很多问题,今日的西方社会科学如果说有什么“问题”,他实际上无法说person,因为这是一个thing, 它包容了很多东西。所谓“人物”就是这个人和别的人不大一样的东西,我或许可以很骄傲的说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从“牛人”说起》,是在说“物”这个概念在中文的意思,“物”是什么?是牛的意思,是各种各样五色的牛,包容整个世界。说这些算是我对
说到人类学学科本土化的过程,人类学这门学科的本土化或建立中国自己的叙述是在1920-30年代这个阶段,最早在吴文藻的身上出现这样的感受,当时在美国的留学学刊上发表《民族与国家》,把世界各国的理论都做了批判,后回来燕京大学,当时就提出了用中国话来讲社会学,刚才说到像中文大学,我听说那里必须用英文或广东话讲,像我这样英文不好、广东话又不会讲的人,到那边和人家交流得时候就会失败。我们早就说社会学要中国化,那么中国化是什么意思呢?(吴文藻)他用中国的语言来讲、用中国的文字来写,并没有像前面所说的学理层面上的,我们中国的社会情况用nation 和states合在一起,然后提出一种叫society这个概念。而只是说用“中国话”来讲就很重要,今天回去看,他有点太简单,但简单里面却含有很深奥的东西,就是说我们社会学里面有没有“中国话”?或者在音乐学里面,即使你用汉语讲,你仍然不见得就是“中国话”。我之所以说大家很幸运,是因为我们在探讨这样一种语言,吴文藻当年以为自然而然的用中文讲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像严复甚至林?那样用文言式的中国话翻译西学,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每个人讲的话都有点像英语式的那种句法,连法语都不大像。务实的说,想寻找一种语言(明白精义)就要寻找一种关键词、关键概念,就是可能带有讲话人的那种本质思想的特制的语言。这里我并不是像汉族中心主义那样要排斥少数民族或者农民的语言,而是说我们汉语学者要清楚,我们的“关键词”是哪一些,最后能够达到跟我们的研究对象的交流。 我们到底用哪些关键词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我最近正在探讨我们关于“人”和“物”的概念,这是最基本的。涂尔干说我们研究社会学方法的最基本原则是要把社会看做一个thing,我们说研究人也好、研究声音也好,可能声音是个“interview”,但是如果你没有把他看成是一个thing, 而且这个thing是跟人不分开的,那么你可能很难领会这个nothing的意思。 其实中国古人对“人”和“物”的关系、内容有很多深入的讨论。我明天到上海大学讲“人物”,西语把人叫person等等,它很明显没有把“物”的意思放进去。但我们说一个人叫“人物”,是person thing??这其实能使我们解开社会科学的很多问题,今日的西方社会科学如果说有什么“问题”,他实际上无法说person,因为这是一个thing, 它包容了很多东西。所谓“人物”就是这个人和别的人不大一样的东西,我或许可以很骄傲的说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从“牛人”说起》,是在说“物”这个概念在中文的意思,“物”是什么?是牛的意思,是各种各样五色的牛,包容整个世界。说这些算是我对 黎志添:我还想说,我们不要受国族主义或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就是说无论中西方,学术研究或知识的再生产有一个条件,不知道是中国的语言还是文化的问题,常常会给我们一个多重的关系的前提,complex,这样的情况对学术和知识的再生产是不利的。 简单的用主/客关系来讲的话,研究中还是有主体和客体的研究,我希望我们的教育系统里要更多地强调研究为知识而研究、我们应该慢慢研究自己的对象,要关注谁在说话。第二是宗教,“宗教”这个词不是好的名词,我很关心这两个字的来龙去脉,有些人在用这个词的时候,根本没有理解西方所谓“人神”之间的关系和态度。中国人在讲一些不能归入“宗教”的信仰时,用popular religion,这个观念不能解释西文中人神之间建立的宗教性关系,反过来如果用西方的宗教观念来看中国也同样看不到之间的关系。所以在研究中一定要用对象所讲的话。 曹本冶:我在思考这个词的时候也请教过许多同事,如
黎志添:我还想说,我们不要受国族主义或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就是说无论中西方,学术研究或知识的再生产有一个条件,不知道是中国的语言还是文化的问题,常常会给我们一个多重的关系的前提,complex,这样的情况对学术和知识的再生产是不利的。 简单的用主/客关系来讲的话,研究中还是有主体和客体的研究,我希望我们的教育系统里要更多地强调研究为知识而研究、我们应该慢慢研究自己的对象,要关注谁在说话。第二是宗教,“宗教”这个词不是好的名词,我很关心这两个字的来龙去脉,有些人在用这个词的时候,根本没有理解西方所谓“人神”之间的关系和态度。中国人在讲一些不能归入“宗教”的信仰时,用popular religion,这个观念不能解释西文中人神之间建立的宗教性关系,反过来如果用西方的宗教观念来看中国也同样看不到之间的关系。所以在研究中一定要用对象所讲的话。 曹本冶:我在思考这个词的时候也请教过许多同事,如 刘桂腾:我昨天就很着急,这两天几位老师的讨论把我想和很多年的问题都说出来了。比如学科的定位,我们用了人类学这么多的理论、概念、方法,那么我们自己是什么?其实人类学对自己的身份,起码在20年前也有困惑,过去说是研究异文化,但对我们非西方的学者来说我们又是在研究“本文化”,这就有点像社会学了,这其实也是在讨论中的。对于我们音乐学来说,自然也有这样的困惑。我很赞同民康说的,有些方法是直接可以用的,比如说“田野工作”等等,可仍然有个问题,并不是说“音乐人类学”称呼一变就变成了人类学的一个分支,那样就没“饭碗”了,搞人类学还用的着我们吗?但还是容易变成“音乐学”+“人类学”,在你的研究中也许音乐形态的部分用音乐学,但是在文化背景和文化分析的部分又会用人类学,要非常清晰地来界定这个界限,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还有就是现在研究中有些学者已经改变了身份了,在民族音乐学中偏重于使用人类学方法的,我称之音乐学研究中的“人类学派”。我们希望从人类学那里拿来一些、借鉴一些,最后成为我们自己的研究。 我还想说说对田野工作的记录和成果的表述。比如现在影视人类学在人类学中发展势头是比较强劲,田野中音频和视频的手段对我们音乐学的研究是很重要的,但实际上得田野工作中,组织者、当事人并没有提到一个重要的地位。我们做一次田野不容易,大多数对象都是“活”的传统,考察的对象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需要格外重视音、视频得手段和技术,包括田野资料采集的规范。上升到另一个层面,人类学比我们的发展高一个层次,他们已经上升到“表述手段”(当然,他们可能不同意我这样说),他们很重视这些技术手段,问题是影视文本和研究(文字)文本的关系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我说的概念不仅仅是记录,音视频究竟有没有被当作一种研究成果的文本来做,这需要我们思考。 萧梅:“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对课题的田野音、视频资料都有档案规定和标准,网上也都公布了。此外,民族音乐学界目前也非常重视影视音乐学,比如ICTM的学术大会,现在每届都鼓励、并专门有以film的形式来做发表的。 王铭铭:我觉得记录还是次要的,要想在音乐人类学学科成为一个能“说话”的人,还是要写作,如果只关注技术层面很容易称为一个学匠,技术性强调过多就忽略了思想。当然,随着技术的发展,各种各样的叙述手段会增多,但是文字写作还是要坚持的。当然,如果为了而课题把对象呈现得更丰满和清晰,当然不排斥。世界上最有名的可能是法国的Jean Rouch,以影像的写实达到学术的效果。但像他那样的人并不多,可能是应为太偏重技术。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有一个这方面的比赛,很容易获奖(“学生电影鼓励奖”),但注意不要变成学匠。 萧梅:
刘桂腾:我昨天就很着急,这两天几位老师的讨论把我想和很多年的问题都说出来了。比如学科的定位,我们用了人类学这么多的理论、概念、方法,那么我们自己是什么?其实人类学对自己的身份,起码在20年前也有困惑,过去说是研究异文化,但对我们非西方的学者来说我们又是在研究“本文化”,这就有点像社会学了,这其实也是在讨论中的。对于我们音乐学来说,自然也有这样的困惑。我很赞同民康说的,有些方法是直接可以用的,比如说“田野工作”等等,可仍然有个问题,并不是说“音乐人类学”称呼一变就变成了人类学的一个分支,那样就没“饭碗”了,搞人类学还用的着我们吗?但还是容易变成“音乐学”+“人类学”,在你的研究中也许音乐形态的部分用音乐学,但是在文化背景和文化分析的部分又会用人类学,要非常清晰地来界定这个界限,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还有就是现在研究中有些学者已经改变了身份了,在民族音乐学中偏重于使用人类学方法的,我称之音乐学研究中的“人类学派”。我们希望从人类学那里拿来一些、借鉴一些,最后成为我们自己的研究。 我还想说说对田野工作的记录和成果的表述。比如现在影视人类学在人类学中发展势头是比较强劲,田野中音频和视频的手段对我们音乐学的研究是很重要的,但实际上得田野工作中,组织者、当事人并没有提到一个重要的地位。我们做一次田野不容易,大多数对象都是“活”的传统,考察的对象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需要格外重视音、视频得手段和技术,包括田野资料采集的规范。上升到另一个层面,人类学比我们的发展高一个层次,他们已经上升到“表述手段”(当然,他们可能不同意我这样说),他们很重视这些技术手段,问题是影视文本和研究(文字)文本的关系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我说的概念不仅仅是记录,音视频究竟有没有被当作一种研究成果的文本来做,这需要我们思考。 萧梅:“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对课题的田野音、视频资料都有档案规定和标准,网上也都公布了。此外,民族音乐学界目前也非常重视影视音乐学,比如ICTM的学术大会,现在每届都鼓励、并专门有以film的形式来做发表的。 王铭铭:我觉得记录还是次要的,要想在音乐人类学学科成为一个能“说话”的人,还是要写作,如果只关注技术层面很容易称为一个学匠,技术性强调过多就忽略了思想。当然,随着技术的发展,各种各样的叙述手段会增多,但是文字写作还是要坚持的。当然,如果为了而课题把对象呈现得更丰满和清晰,当然不排斥。世界上最有名的可能是法国的Jean Rouch,以影像的写实达到学术的效果。但像他那样的人并不多,可能是应为太偏重技术。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有一个这方面的比赛,很容易获奖(“学生电影鼓励奖”),但注意不要变成学匠。 萧梅: 王铭铭:从这个角度讲,我刚才说的不对。 周楷模:通过各位特别是刚才三位学者的讲述,我有一个很共同的认知,就是本土化建设。前面都在强调本土化建构的问题,里面有两个范畴,就是如何进行本土化的建构和在建构中如何进行借鉴。我们如何进行本土建构的前提是我们对自己了解了多少,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建构自己?我们所面临的困境就是摆不平各学科之间的关系,而其中更重要的是不了解自己的定位。 前面
王铭铭:从这个角度讲,我刚才说的不对。 周楷模:通过各位特别是刚才三位学者的讲述,我有一个很共同的认知,就是本土化建设。前面都在强调本土化建构的问题,里面有两个范畴,就是如何进行本土化的建构和在建构中如何进行借鉴。我们如何进行本土建构的前提是我们对自己了解了多少,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建构自己?我们所面临的困境就是摆不平各学科之间的关系,而其中更重要的是不了解自己的定位。 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