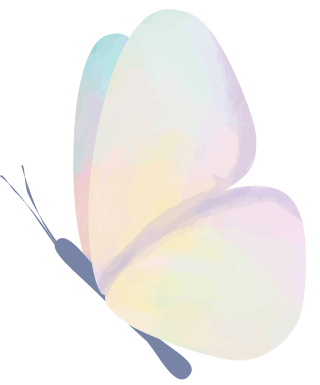(2020年5月)【新书推介】魏育鲲《湘西苗族仪式音乐研究》
0
1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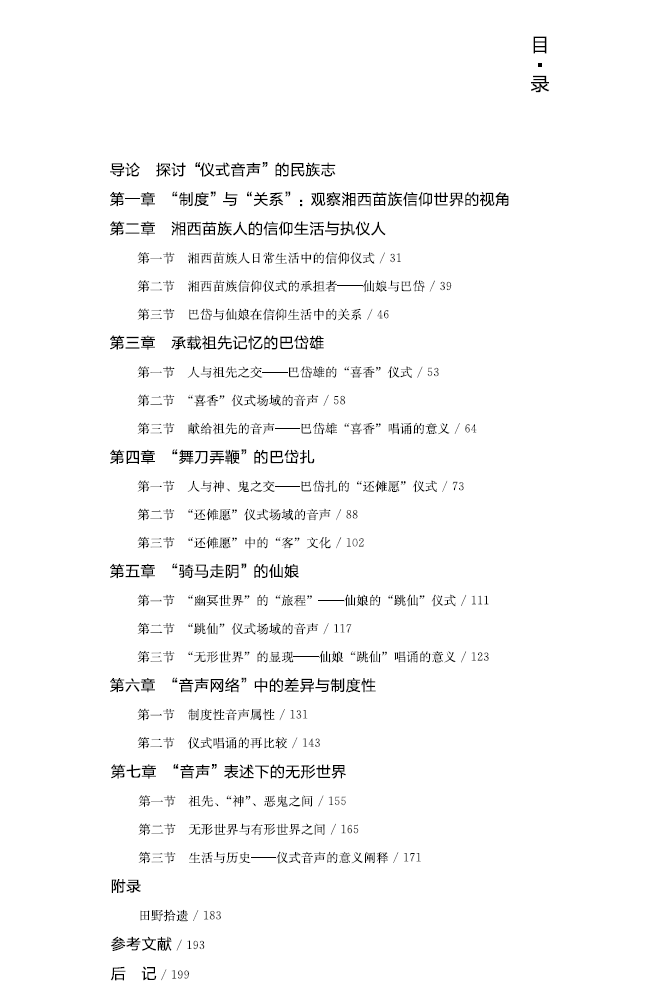
03
魏育鲲《湘西苗族仪式音乐研究》一书是由她6年前的博士论文《仪式音声表述下的信仰世界——湘西苗族仪式音乐调查研究》修改而来。除了将论文中的绪论依据重点拆分成扼要梳理湘西苗族在民族混居中的历史语境、强调越出单一类型的信仰仪式而从三种执仪人及其执仪探讨湘西苗族生活全景中的仪式音声的必要性、以及就前人在信仰仪式以及民族音乐学领域对湘西苗族的研究回顾之【导论】,和论述该研究所采用的“制度”与“关系”作为观察湘西苗族信仰世界的介入视角之【第一章】外,其他的内容基本保留了博士论文的原貌。若非其他原因,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该书的标题应恢复“信仰”一词。
这几年给学生的著述写序之事渐渐增多,每次提笔,意味着回忆。
首先是选题。
和一部分在博士阶段改换硕士研究领域的学生一样,魏育鲲的博士论文选题与她在硕士阶段对凉州“贤孝”的研究相距甚远。这个原因一方面与我自己在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的任职有关,另一方面则因为她自硕士毕业就一直在地处湘西的吉首大学任教有关。2008年她第一次考博未果,我和上海音乐学院的两位同学就在暑假来到吉首,展开湘西苗族和土家族民间信仰初步调查。魏育鲲作为半个向导,和我们一起走访了吉首、保靖、古丈、龙胜、永顺、花垣几个县,接触了巴岱雄、巴岱扎、“仙娘”三种执仪人及其执仪活动。2009年她成功申请了“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的课题“湘西苗族信仰体系中【苗—客】巫乐比较研究”,2010年通过上海音乐学院的博士生招生考试后,又与当年的另外半个向导、一起做调查的苗族学者吴华强一块儿,再次得到“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的课题“湘西苗族‘跳仙’仪式音乐的调查与研究”的资助,如此选题也是顺理成章。
不过,在是否将“仙娘”纳入博士论文的研究中,魏育鲲在开始是有纠结的。最重要的原因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我不信这一套”。当年我因为研究广西壮族的“魔婆”(当地学者现在多用音译“乜末”指称)、娅禁等仪式音乐,而扩展至跨地域的音乐与迷幻(trance),魏育鲲虽然也曾于湘西同行,但她是“冷眼看戏”,兼带怀疑。确实,我所接触的许多读者或听众每每关心的是所谓的“萨满”与“巫”是真是假?更有人或因历史偏见视之“迷信”以至相歧。相当一段时间,在讨论天人鬼神的交通类型上,学者们在学理上或讨论庄子之气与心斋,或者讨论易传与占卜,或者是屈原之“出神”,又或者是礼乐之天人合一,却往往视那些在仪式中进入“附体”“出神”或“迷幻”的灵媒、乩童、仙姑等为下层末法。然而,这些被视为残缺“小传统”的民间信仰,实际上却与中国民间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对其信仰仪式音乐的研究,一方面可以直指音乐的效应,它不仅仅局限于音乐生理、心理、神经生物、意识变化等学科一直以来的探讨,也可以为作为人类通过音乐效应认识自我铺设基础,进而探索音乐力量以及人类意识现象;一方面可以触及其仪式音声作为一种结合自然与文化的能量,究竟在天地人神之间有何作用、并如何作用,以探索人是如何制造、使用并理解“音乐”的;此外,相应的仪式音乐研究,依然是探讨仪式音声作为信仰的“现声”,如何能够体现出社会文化内涵和宇宙观,并赋予仪式音声宗教学的含义。而真假的判断倒是次要并应“悬置”的。
正是在对“跳仙”仪式的调查与研究中,魏育鲲体会到就湘西苗族信仰世界中三种执仪人及其种类繁多、功能各异的执仪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恰恰可以展现他们的宇宙观和生活世界耦合而成的共生整体。只是在当时,多数的仪式音乐研究还是偏重于个案的调查,选择一个地区的族群中不同教门或种类的仪式音乐做研究对象,题目会不会太大呢?好在魏育鲲之前已经分别在两个课题中就三种执仪人及其执仪有了一定的调查基础,并在田野中与他/她们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为论文写作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材料。其时,“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的课题规划中,亦明确提出了“仪式音乐的地域性与跨地域性、传统与变迁的个案与比较”的研究方向。此外,在我自己以壮族“魔仪”为出发点并扩展至北方萨满及境外“巫乐”的研究中,深切地感受到过于专注某种信仰或宗教文化的纯粹定性和区别,如制度的、弥散的;本土的、外来的;中国的、外国的;大传统、小传统,难免忽略历史过程中文化之间的互渗互融。因此,谱系的考掘与非同源性的比较研究,将为我们更深入的辨析和理解民间信仰仪式在历史过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错并存与演变延续。2010年我在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的第四次讲习班的报告中,就以“中越边境‘巫乐’考察”为例,阐述了在“关系主义民族志”视角下,开展谱系学研究与比较的重要性,并以研究实例,具体地阐述了如何以制度性展演与制度性音声属性两个方面作为比较的抓手(这些研究后来陆续发表于2012-2013年《民族艺术》的“巫乐研究专栏”)。
因此,由“制度”和“关系”为切入视角,应该是当时我们师生鉴于实地考察的切身体会,以及与人类学界互动的一个结果。正如魏育鲲在答辩中和答辩后就为何使用“关系”作为视角的思考:
论文最初的思路是选择湘西苗族某一类仪式的音声展开分析与研究,但是随着对当地人生活的进一步了解,发现当地不仅仪式类型丰富、多样,而且还存在不同职能的仪式专家,他们共同支撑了当地人的信仰与生活,是包容在特定空间中的“整体”。接下来的问题是,该如何去审视和理解这样“混杂”的信仰现实呢?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总是不得不注意到不同仪式和仪式专家之间的差异、共性以及互补关系。也正是这样,我以“关系主义民族志”为方法呈现这部湘西苗族人“整体”信仰生活的音声民族志,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即是:什么事物不是在关系中呢?它被强调的意义是什么呢?而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正是由于任何事物都处在关系之中,以“关系”来解读更显必要。因为任何事物的样态并非在自我定义中完成,而是透过与其它事物的比较才得以显现,并且常常因坐标不同而不同。也正是在关系中审视,我才更清晰地观察到 “苗”“客”巫师与“祖先”“神”“鬼”以及“主”“客”“陌生人”等概念间的某种对应。(选自魏育鲲曾经交给我的作业)
当然,就“制度”的切入点而言,魏育鲲的研究主要关注了三种执仪人所执祭仪的制度性音声属性,目的是为了在变动的关系中观察仪式中显现的稳定而具有不可改变的特征,它们指明了声音与仪式意义之间的特定关系,也意味着一个群体对一套传统价值的认同,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共享、共识的“默会知识”。事实上“制度”并非仅是文化结构层次中的较大单位或体系,可以说,各种文化中的诸多能够被共享意义的行为都具有“制度”属性,因而“制度”不仅可以是分析对象,同时也是一种方法。魏育鲲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生存的民间土壤虽然少有如‘礼乐制度’这样的‘成文法’对音乐生活进行规范,但事实上音乐之所以能够在民间生活中以某种形式展现并被接受,以及形成我们所观察到的不同地域独特的音乐风格、用乐方式及乐人组合,都是当地传统、习惯等等非正式制度的产物。与乐相关的演出场合、参演人员、使用方式甚至多种音乐形态一旦可被辨识、接受、遵守,从本质上就已经成为某种非正式制度。”比如如何理解不同种类的执仪人的师徒传承制度、神启制度,比如在制度性音声属性中,考察“三类仪式专家在具体的仪式场域之中仪式音声的发出、展现的方式以及其具体的音声形态;三类仪式专家之仪式音声之间形成的结构关系;人们如何通过组织仪式音声表征信仰内涵”,进而观察它们形成的文化机理。“从这个意义上说,仪式音声本身及行为形成的一系列‘制度’,是行为层面(仪式展演、仪式音声)与思想层面(信仰)的中间层,诚如庞朴所言,通过对中间层——制度层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获取对思想层面的认知,那么把握仪式音声本身及行为的‘制度’则可以成为探讨仪式音声与信仰之深层关系的有效方法。”
当然,魏育鲲的论文尚未及更清晰地阐述制度、制度性、制度化的概念及其关系和过程,而在“跳仙”仪式中,那些被安抚、询问的各种“野鬼”等颇有意味的声音现象也尚未进入她的进一步探讨等等。
魏育鲲给我的印象是双重的,一重是她在阅读和面对研究对象时的直觉、冷静及概括的能力,并且常常冒出独到的见解;另一重则是她常常在生活和学习中流露出的一种任性。除了天分,前者基于她常年喜欢阅读和分析,多多少少也与她在硕士阶段曾经受教于牛龙菲先生有关;后者则与她从小的经历及个性相关。本来,身为导师,我不该就后者干涉太多,但如果这种个性影响到学术,就有必要“修正”。
记得她刚入学,恰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举办题为“流与变:全球视野下本土音乐资源之诠释——两岸三地民族音乐学论坛”的研讨会,基于曾经读过她的阅读报告以及日常对学术问题探讨时的印象,我把撰写综述的任务交给了她。没想到,初稿一交上来,我差点儿直接背过气去。原来,她因为自己对发言内容的喜好,将一篇综述写的七零八落。又有一次,我交给她一个为《人类学评论》撰写书评的工作,结果又是只有摘引没有评论的敷衍之作。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发现她去烫了个刘海儿,打扮的像个电影明星,那一次,我严厉地批评了她。记得我当时的原话是:“妩媚救不了你,记住,只有露出的额头才是智慧的”。不知道是因为我太严厉了,还是她真的听进去了,多少年过去,她一直就没有改变过自己露出脑门的形象。直到今年,我在与一群毕业了女生聚会的时候,听到她们在议论自己的发际线,我突然就心疼地对魏育鲲说:“哎,你要不还是把发型改了吧?”
魏育鲲的从业之路并不平坦,考博三年,毕业后在扬州大学工作了两年又到中国音乐学院做博士后,原定毕业之后继续仪式音乐研究的方向又转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课题。当然,从学识的积累来说,这些辗转皆非无用功。但我还是想对她说,虽然人生际遇不如意事常八九,但有时动不如静,静则能走自己的路。这也是我希望魏育鲲在博士后出站后,能够回到西北,回到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走自己的路!
萧梅
2019年12月4日于上海驿站
04 附录·田野拾遗(节选)
想阅读更多内容,
欢迎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跳转购买链接。
谢谢您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