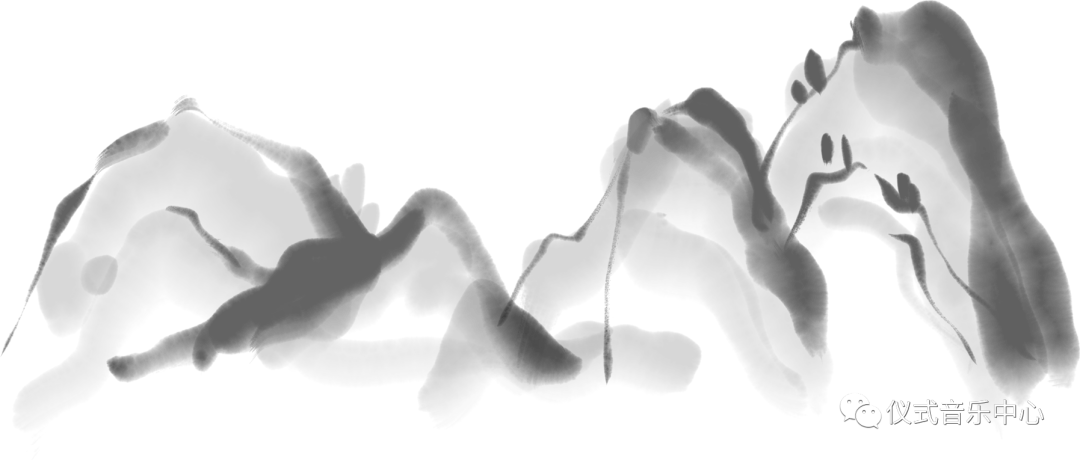音乐人类学专题研究课堂汇报(14) | 世界体系中的民族志:多点民族志的出现
《音乐人类学专题研究》是上海音乐学院2020-2021学年第二学期的研究生课程(授课教师:萧梅教授)。本课程以一个学期16周的课程为整体规划。第1周的“引论”介绍课程基本内容、目的与课程安排,并讨论关于此课程的相关概念与定义。之后的14周课程则包含五个单元的内容,分别为:音乐人类学实地考察与民族志写作问题;音乐体验与音乐表演民族志;历史音乐人类学专题;仪式音乐研究;应用民族音乐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课上,同学们以专题汇报以及理论研讨的方式参与课程学习,仪式音乐中心也将陆续推出同学们在课上的汇报内容,敬请关注!
本期推文共推出二组同学的汇报,即《寻访与见证——海南民俗音乐60年》与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世界体系中的民族志:多点民族志的出现》)。另外,课堂研讨部分附在本期推文“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下方,供大家阅读。本课程汇报意在推进教学和交流。未征得报告人同意和授权,不宜引用或转作他用。
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
汇报人:
陈亦(电子音乐设计专业/2019级硕士研究生)
董赫(爵士钢琴音乐人类学专业/2020级硕士研究生)
同学们,老师们大家好!我们小组汇报的文献主题为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世界体系中的民族志:多点民族志的出现》)。这篇文章主要围绕着“民族志”以及“多地点民族志”这两个话题进行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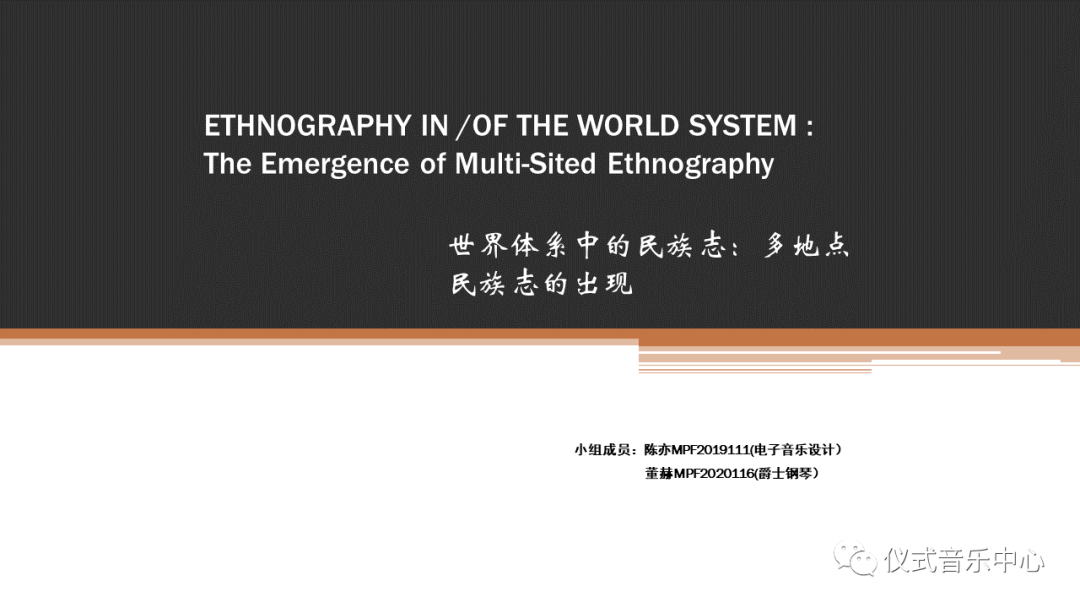
“民族志实践的长期模式如何适应更复杂的研究对象?”作者在摘要中即提出这样的问题。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志学者所面对的对象愈来愈复杂和多样。于是,一种民族志方法论转向——“多点民族志”开始出现。
文章围绕着这一转向展开讨论,一共分为5个部分。如ppt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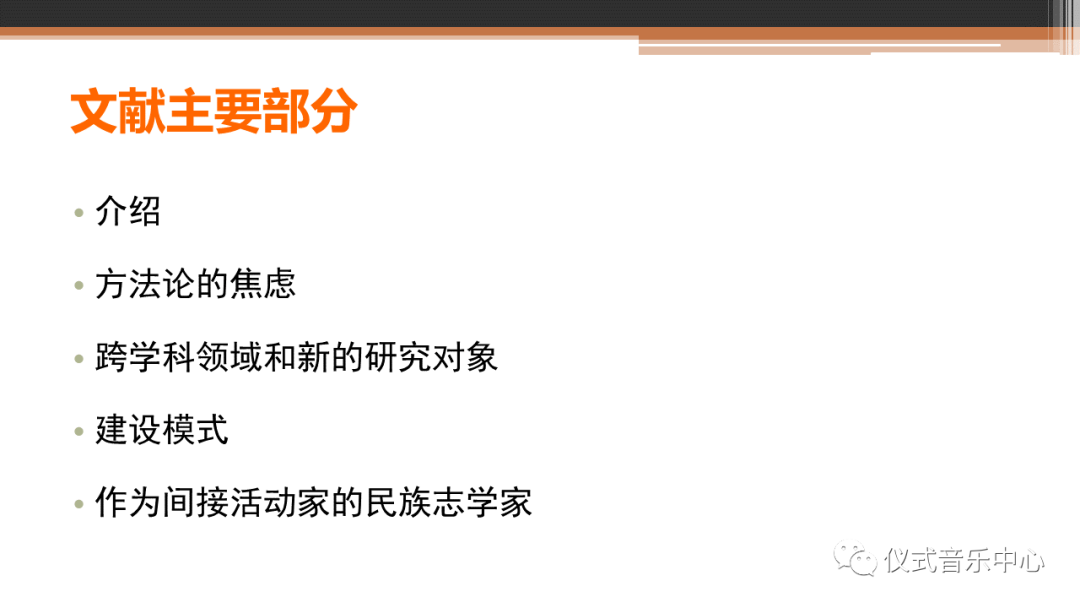
第一部分是介绍。作者在这一部分花了大量的笔墨来说明何为“多地点民族志”。除此之外,还介绍了它的历史背景、研究对象等。
文献中首先提到了民族志的两种模式。最常见的模式为集中于单一地点的民族志的参与观察,同时以其他方式方法发展世界体系语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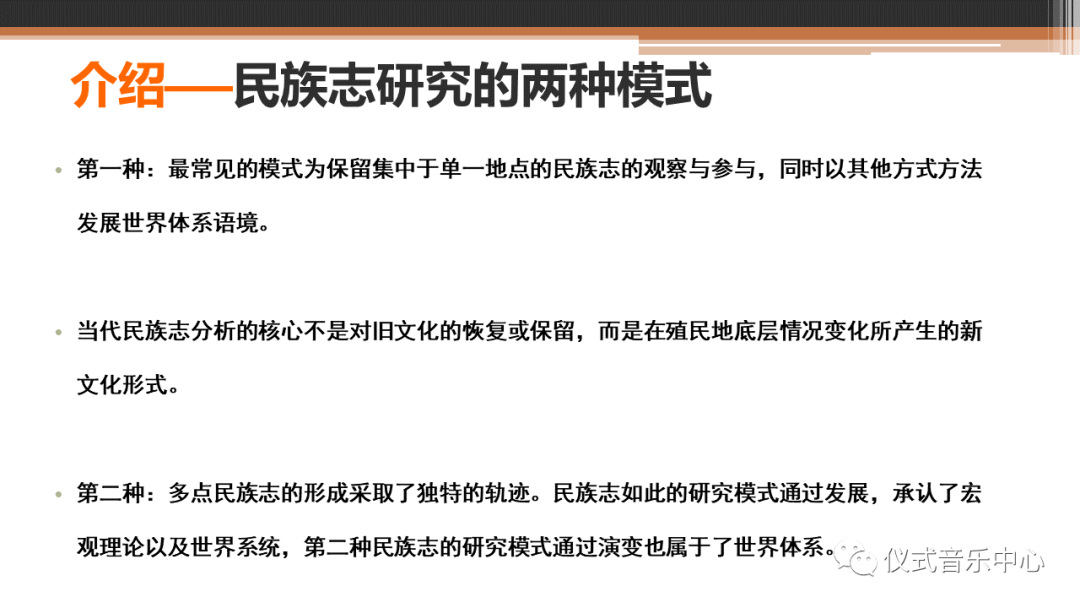
作者认为当代民族志分析的核心不是对旧文化的恢复或保留,而是各个殖民地底层情况变化所产生的新文化形式。这些以新文化为研究主体的民族志研究,是流动的、多点的,是嵌入在世界体系中的,于是第二种民族志方法应运而生,即多点民族志,它有其独特的轨迹,流动于世界之中。
世界系统发生了变化,由此产生的新的概念不被完全理解。所以在这个前提下,作者提出了他所思考的问题:多点民族志研究探索的意义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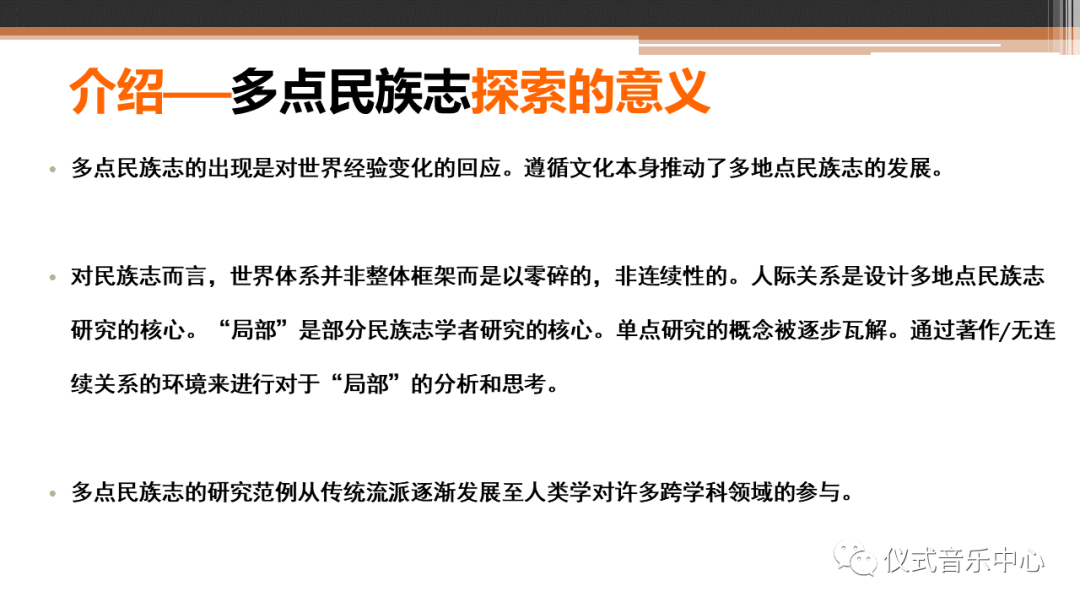
作者认为多点民族志的出现是对世界经验变化的回应。文化本身的变化推动了多点民族志的发展。对民族志而言,世界体系并非整体框架而是零碎的,非连续性的。“局部”成为部分民族志学者的核心,单点研究的概念被逐步瓦解。多点民族志的研究范例从传统流派逐渐发展至人类学,且有许多跨学科领域的参与。
第二部分为方法论的焦虑。文献中提到了三种关于方法论的焦虑:对挑战民族志极限的担忧、对田野力量减弱的担忧以及对“底层”消失的担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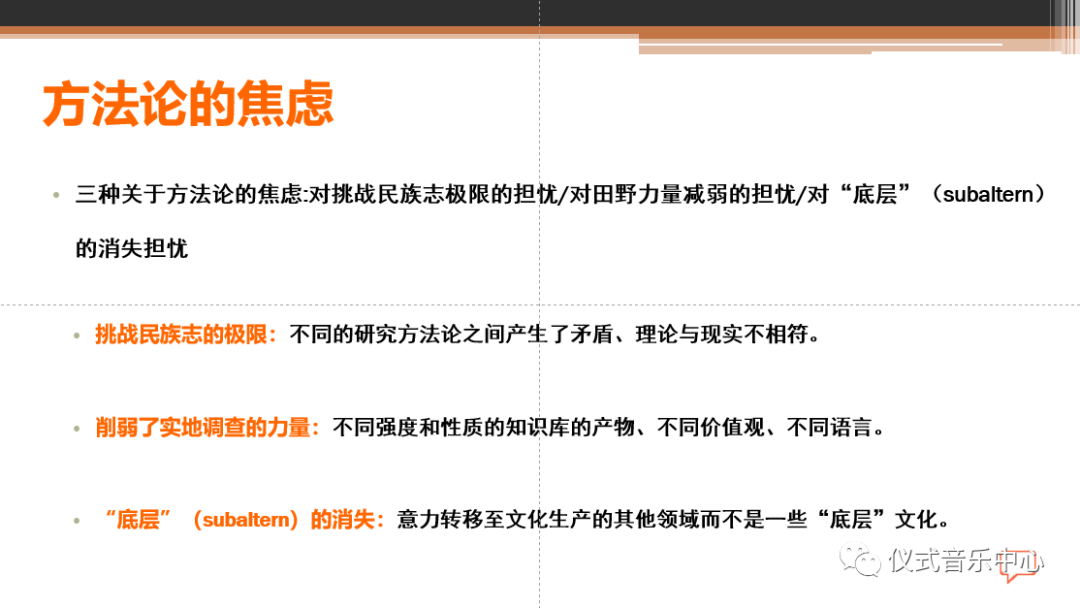
对挑战民族志极限的担忧主要在于民族志研究开展的范围内,不同研究方法论之间产生的矛盾。此外部分研究得出的理论与民族志研究所面临的现实不相符。
对田野力量减弱的担忧,是由于作者对多现场实地调查的可行性抱有存疑。多点民族志是不同强度和性质的知识库的产物。在多地点研究中,不同考察地点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地区之间语言的不同和转译......这些都超过了传统的实地调查的限制。
接着在“底层”的消失这一部分里,作者提到多点民族志必然会把注意力转移至文化生产的其他领域而不是社会底层的人与文化。并且提出了要关注底层人的观点,不能一味地“向上”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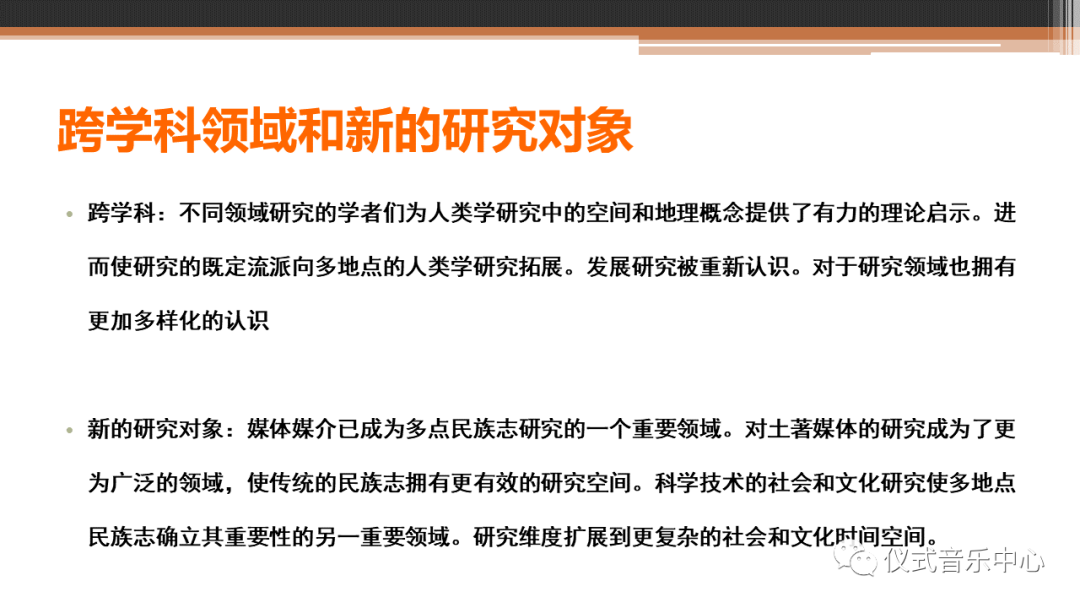
第三部分是跨学科领域和新的研究对象。作者认为多点民族志的研究对象所处的当代文化环境,是被后现代主义理论与高度资本配置所激发的。在分散的文化研究领域,跨学科研究解决了人类学长期关注的区域研究,挑战了“定点”文化的旧做法。不同领域研究的学者们为人类学研究中的空间和地理概念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启示。部分研究被重新认识,对于研究领域也拥有更加多样化的认识;而科学技术的社会和文化研究是多地点民族志确立其重要性的另一重要领域。例如,媒体媒介成为多点民族志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特别是土著媒体的研究,这样的研究使传统的民族志拥有更有效的研究空间。
第四部分主要介绍和分析了多点民族志研究的建设模式。作者将其分为7个部分,如ppt所示:

首先,“跟随民众”是最传统的多点民族志研究模式。通过跟踪考察民族志对象,发现其在不同地点间的联系,从而建立系统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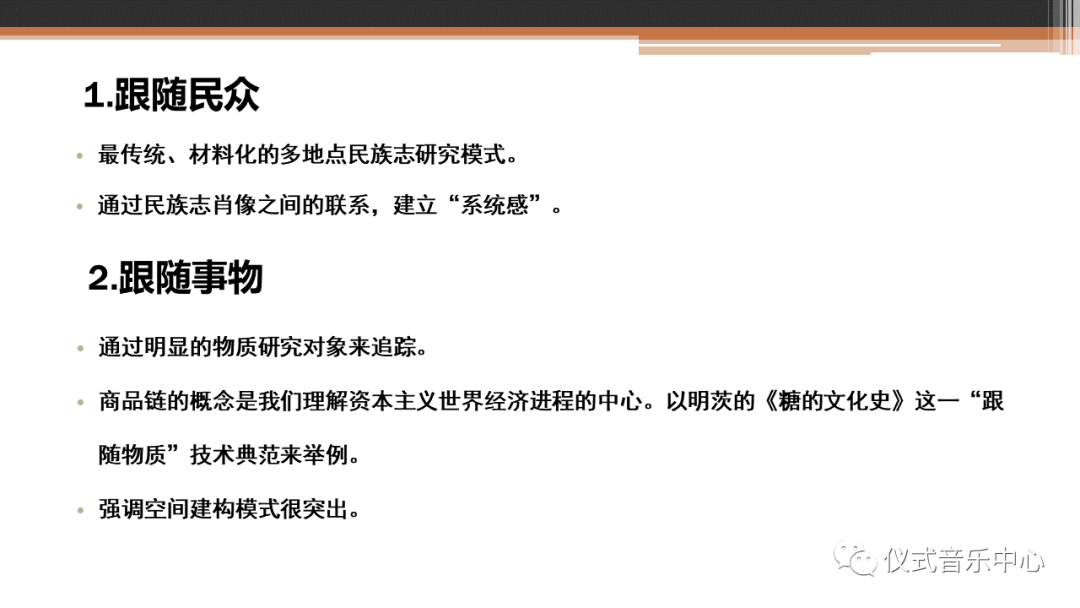
在“跟随事物”这一部分中,作者认为跟随事物可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过程中的文化研究最常见的方法。商品链的概念是我们理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进程的中心。作者以美国学者西敏司(Sidney Mintz)《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这一“跟随物质”的典范为例,强调“跟随事物”中空间建构模式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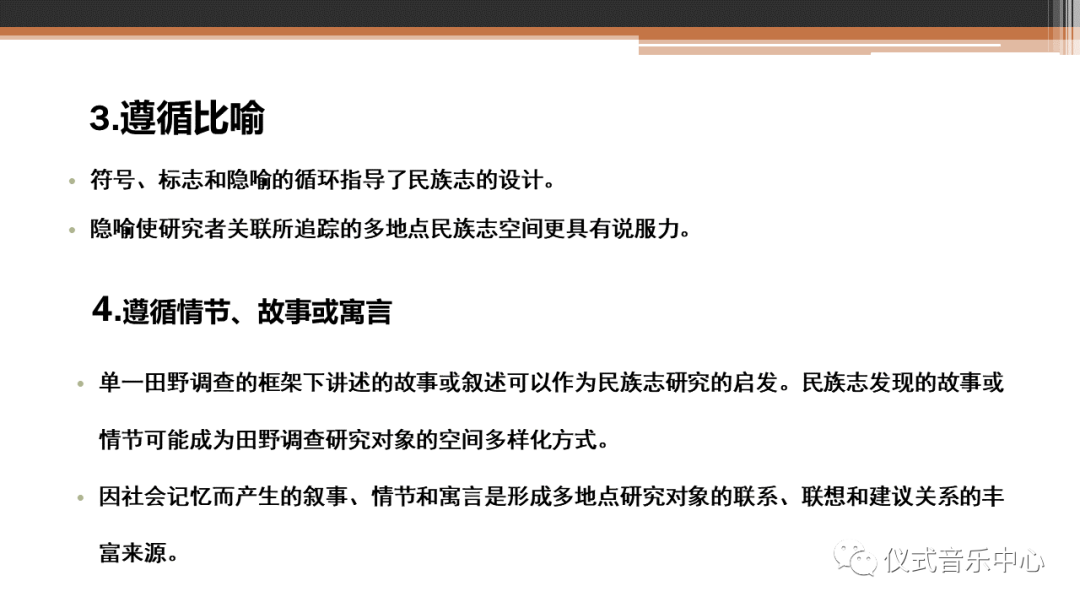
“遵循比喻”这一部分主要提到了符号、标志和隐喻的循环指导了民族志的设计。作者认为隐喻使研究者关联所追踪的多地点民族志空间更具有说服力。
接下来是“遵循情节、故事或寓言”,作者认为单一地点考察的框架下,讲述的故事或叙述可以作为民族志研究的启发。民族志发现的故事或情节可能成为研究者研究对象时展现空间多样化的方式。因社会记忆而产生的叙事、情节和寓言是形成多地点研究对象的联系、联想和建立关系的丰富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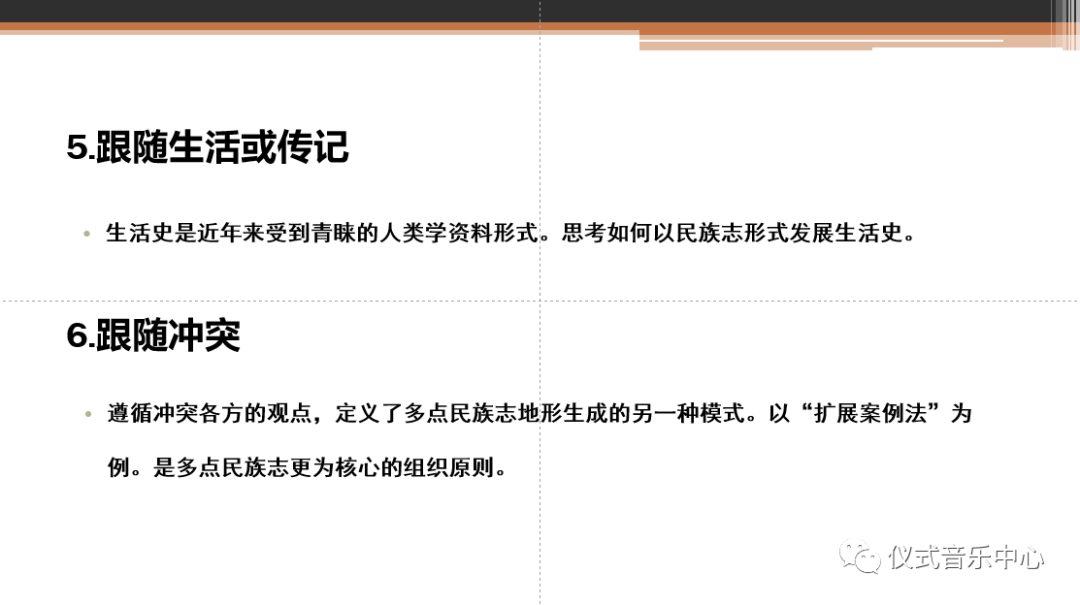
“跟随生活或传记”中提到了生活史是近年来备受青睐的人类学资料形式。并且思考了如何以民族志形式发展生活史。
在“跟随冲突”中,作者遵循冲突各方的观点,以“扩展案例法”为例,定义了多点民族志生成的另一种模式。作者认为跟随冲突是多地点民族志更为核心的组织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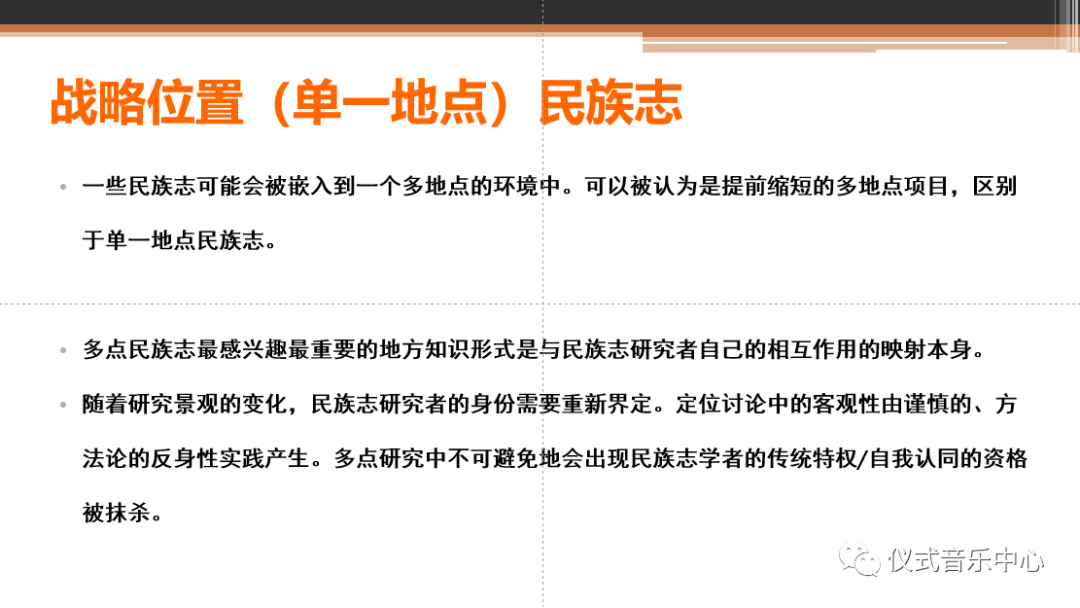
“战略位置(单一地点)民族志”会被嵌入到一个多地点的环境中。战略位置(单一地点)民族志可以被认为是提前缩短的多地点项目,区别于单一地点民族志。
另外,多点民族志最感兴趣、最重要的是,地方知识与民族志研究者自己的相互作用和映射。随着研究景观的变化,民族志研究者的身份也需要重新界定。多点研究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民族志学者的传统特权/自我认同的资格被抹杀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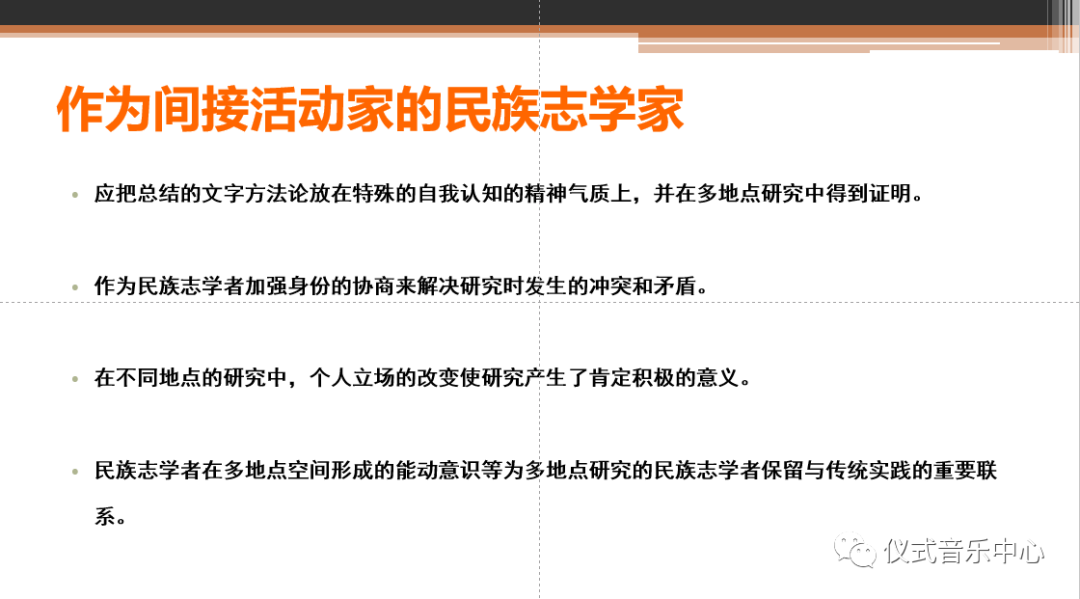
“作为间接活动家的民族志学家”是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作者认为应把总结性的方法论放置于特殊的自我认知中。同时作者也提到了作为民族志学者应加强对自我与他人身份的考量,来解决研究时发生的冲突和矛盾。民族志学者在多地点空间形成的能动意识为多点研究的民族志学者保留与传统实践的重要联系。

这就是我们小组对于这篇文献的汇报内容,谢谢大家!
课堂研讨
2021年3月31日
萧梅老师:尽管每个小组都超时了,但同学们的汇报状态保持的很好。不过我建议大家可以把汇报的讲稿写出来,这样你就可以预计自己的发言时间。国外的学生参加国际会议,老师必须让他做一次试讲,如果你的汇报超时,可能会影响到人家对你的学术水准的看法。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课堂汇报,它能够让你得到锻炼。另外,我觉得大家PPT做的很好,都能将阅读内容精简准确的予以提炼。
我们这一节课的阅读内容是想要突出 “怎么撰写田野笔记或音乐民族志”。第一组同学的汇报“Dancing in the Field:Notes from Memory”【汇报内容参见“音乐人类学专题研究课堂汇报 (9)”】,把“Embodiment”翻译为“化身”。这个词现在有很多翻译,有人翻译为“具身”。它与认知研究相关。比如身体的活动方式、身体感和运动体验与我们认识和看待世界相关。虽然我们也曾说关注概念、行为和音声之间的关系,比如身体行为,但身体或身体行为也可能是被静观的一个被放于某地的对象。所以,在身体的研究中如果只是将其作为一个被观看的物,那它往往就是一个缺席的在场者。所以,“Embodiment”它实际上想强调一个动态过程中身体与认知的密切相关性。因此,社会的文化观念、习俗也可以通过一个具体的身躯活动体现出来,所以我们也常用“体现”两个字。但是,我自己是选择“缘身”、“缘身性”或“缘身而现”。为什么把它翻译成缘身呢?因为,它更强调那种身体体验在境域中重重缘发、相互指引的过程,而缘身性体验只是分析人类介入和参与世界的一个起点,并不意味着文化与身体体验在结构上的一致。如果我们把表演视作一个动态的过程,那么这个身体是在一个情境中表达出来的,它不是一个“死”的东西,是开放的。最关键的是,要把“Embodiment”看做是一个未决的方法论,它不是必然的。其实我们搞音乐的人非常理解这一点,比如我不知道我今天的演奏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它不是一个已经被决定了的东西,而是一个可能性。针对第一组同学的汇报,我还有一个建议,你们刚才汇报将“field”翻译成“野外”。这里的Filed不是野外,我建议这个“field”可以翻译成“现场”。fieldwork本身可以说是一个现场作业,那么我们这里也可以说是一个现场,因为它是一个讲述田野或现场中的舞蹈。
我觉得这篇文章还有一个特点,虽然田野笔记是碎片化、转瞬即逝的,没有关联的。但你把它记下来,最后你在写作论文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笔记有多重要。另外我想请大家注意去看作者田野笔记的书写方式。因为在我的个人经验中,很多同学在写作文本时常常漏掉细节,也就是说我们的笔记很喜欢概括。比如我要跟你们说今天这个课堂上发生什么事情,你们很可能去做总结,然后抛出很多概念。但是田野笔记切忌用自己的概念去描写,而是尽可能把你所看到或者你身临其境的东西以最为白描的手法记录下来。比如说我们到食堂去,你就说,噢,食堂里在卖馒头。可你如果让苏亚人看这份笔记的话,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馒头,因为这个“馒头”是我们汉人这个文化的人才知道的概念,而就算是上海人概念中的馒头,和北方人就不一样,是包子。所以,你的田野笔记尽可能不要用特定的称谓和概念,而是尽可能的白描,你可以将它的模样描写出来,然后一步一步地去解释他。这样你才能让另外一个文化的人了解,而且你也不会误解你所看到的那个文化的事物。但是我们很多同学在田野考察的时候,就不愿意这样详细地去描写对象。在田野考察时,如果我今天要去学习他们的歌唱,我们就需要详细地白描,比如如何发声?是用平舌还是翘舌发音?你的描写一定要有细节,因为你的描写越有细节,将来你对这个文化的发现就越深入。我这里举几个教学中的例子,大家可以看看原文与评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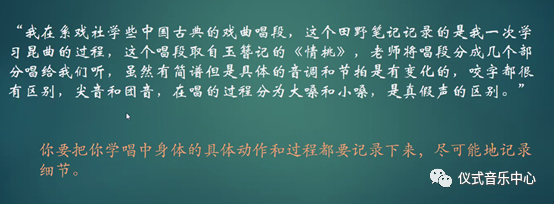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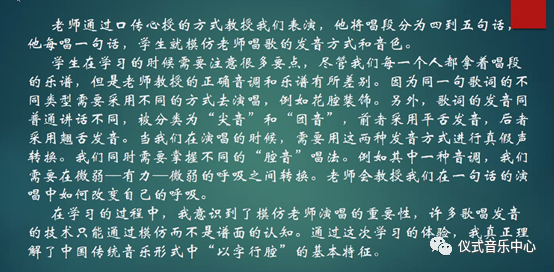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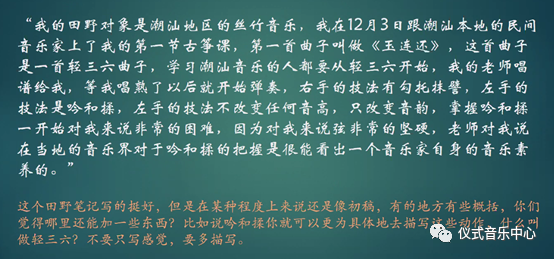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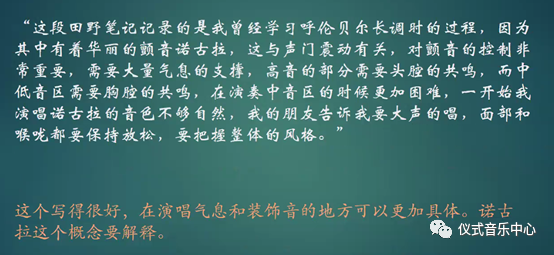
正是因为我们前面的观察是非常细节的,那么之后的写作就很重要了。伴随描写的另外一个窗口就要分析和归纳,所以“双窗口”的作业是音乐人类学非常重要的一点。当然表演专业的同学们也可以用“双窗口”的方式去记录你上课或者你听其他同学的音乐会。比如老师的教学是怎么样的,演出的整个场景又是怎么样的;另外一个窗口是你对这些内容的分析,当你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形成一篇有关表演的非常好的论文。“描写”和“如何描写”是我们音乐学专业的基本功。因此我让大家去看西格尔的《苏亚人为什么歌唱》【汇报内容参见“音乐人类学专题研究课堂汇报 (12)”】以及Sally Ann Ness的 Dancing in the field: notes from memory,里面都有非常好的描写。
接着谈另外一组。George E. Marcus的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是人类学中很重要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我不知道有没有中译版,大家可以去找找。你们小组在汇报这篇文章时,提出“subaltern”一词是否应该翻译成“次等人”的疑惑。我建议当我们遇到这样的词时,可以将词所在的上下文一起呈现出来,也可以在旁边用一个括弧把英文原词放进去,这样我们大家可以去讨论。多点民族志的提出,无疑是针对我们原来单一且长期的田野。因为,当下随着全球化,很多东西都处在流动的状态,多点民族志也常与跨国研究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某一种音乐类型从某地到某地,它在不同的国家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如果我们以这个案例做民族志,就需要研究者围绕这一音乐类型跟踪考察,也就是在一个全球体系中,我们很多研究不再是去追求一个根源、根性,或某一音乐文化的本来面貌和“原生态”。事实上,“原生态”在当前的时代环境下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现在所谓的打引号的“原生态演员”去到世界各地演出,参加艺术节,他在不同的地方参加不同的艺术节,他的演唱生态都会发生改变。所以说,他的每一个现场都应该是我们关注的方面。那么,我们这时就发现事件已经是碎片化了的,我们要研究这种碎片化事件的时候,就需要以动态的观点去做分析。它是不是截然跟过去没有关系呢?答案当然不是的。动态的世界需要我们用一种动态的方法论去研究,所以多点民族志就是让我们更注意路径,从它的根到它如何在不同的地方被吸融、改变、影响。但不管怎么说,有一个不变的东西,他们都是研究一个文化的在场。实际上音乐表演就是一种文化,苏亚人的世界将音乐视为文化,我们在苏亚人社会中看到一个村庄就是一个音乐厅,一个苏亚人的世界。所以,音乐人类学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认识论,它一直在解决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极具本体论色彩的。西格尔的“Long-Term Field Research in Ethnomusic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也是非常重要的,他所反思的长时段田野带来的问题,正好是我们在研究自己本国本民族音乐时相对的“短时段”的一个对照。
“我怎么样去做研究”?杨沐老师的这篇《寻访与见证:海南民俗音乐60年》,我也是希望大家去了解杨沐老师是如何去发现问题的,从他在大学期间和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同学们到海南采风,生发问题意识,并一直选择在这里研究。沈洽老师的《民族音乐志的架构》、《贝壳歌》【汇报内容参见“音乐人类学专题研究课堂汇报 (11)”】,我认为也非常值得大家认真琢磨,包括不同时期的不同提法——音乐民族志?民族音乐志?等等。大家可以将这两篇文章放在一起来讨论。
文字/图片:陈亦、董赫
编辑:罗晗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