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莹|2025年 “少数民族唱法实地考察与数据分析研修营”学员随想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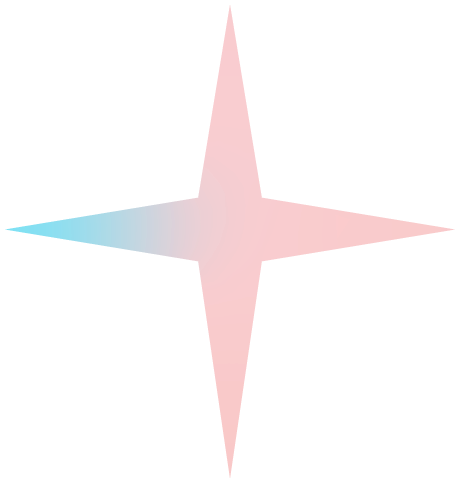
2025年7月25-31日,少数民族唱法实地考察与数据分析研修营圆满结营,学员们收获颇多。下文为即将就读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的孔莹同学在研修过程中的所见、所思、所感。
一、走进少数民族唱法:
从培养一双“文化耳朵”开始
此次研修营是我第一次有规划、有针对性地学习与考察少数民族“唱法”。理论阶段的三天里,在各位老师们的带领下,我初步了解了多种唱法类型。出发前,我还查阅了相关文献,对考察民族的背景与唱法做了功课。然而,田野的第一天就让我各种“碰壁”。当我带着既定目标,将所有的关注点聚焦于“唱法”时,才发现每一首歌调中居然有如此多的唱法,并且彼此交错、变化无常,就连那些我原以为熟悉的唱法,在现场也变得难以辨认。我开始疑惑,到底是什么影响了我的判断?
比聆听唱法更难的是采访。即使是最基础的“你多大了”这样的提问,也会因语言差异而受阻,更遑论直接询问“唱法”是什么。无奈之下,我只好将前人研究中已经考察出的唱法名称模仿给歌者们听,试图打开沟通的窗口,但效果并不理想。
最后,我放下功利性的提问,尝试把关注面向更广的演唱实践。结果,许多与唱法相关的细节竟慢慢浮现出来。比如,阿尔麦藏族歌者形容好听的声音应像“水波浪”一样,而在一次关于演唱队形的提问中,泽英俊老师提道:“多人演唱时,‘得拐’‘尔拐’要交错站位,在不同时机演唱‘嘎古’,营造出此起彼伏的声音效果,这样才好听。”听到这番话,我立刻联想到,这或许是上述“水波浪”唱法的形成机制。

学员们采访阿尔麦藏族歌手
慢慢地我意识到,唱法的考察不应被预设为一个能够在短时间内,通过几次提问就可以完成的“技术清单”,而是一整套深深嵌入在地方生活和社会关系中的声音实践。正如萧梅老师在评价洛马克斯(Alan Lomax)的歌唱测定体系时所指出的:“尽管该体系的采样来自于各社会的行家里手,注明了包括演唱方式、规模、性别、年龄、演唱地等背景材料与文字说明,但还是忽略了各社会歌唱围绕声音产生而存在的‘地方性知识’及其传承惯例。所以,不可能获得相关族群的‘歌唱’‘发声方法’及其蕴含的一整套包括形态、技巧、审美、评价标准的声音概念,也不可能探索到这些概念对于一个族群文化和社会的象征意义。”这让我更加明白,声音的生产、唱法的形成从来不是孤立的技巧,它的形态、变化与传承,都深深扎根在歌者及其生活环境中。
至此,我解开了心中的疑惑:第一次踏上阿坝,一切对我来说既新鲜又陌生。因缺乏长时间浸润所积累的文化感知,面对那些我原以为熟悉的唱法,才会暂时“失去”了原有的耳朵。那种无法准确捕捉和理解声音的感觉,让我体会到,聆听绝不仅仅是生理上的行为,更是一个深植于文化语境中的复杂过程。正如徐欣老师在前几日讲座中提到的,在跨文化的聆听中,“聆听”究竟是物理问题还是文化问题?不同文化背景塑造了人们对声音的期待、理解和评价标准。一个未被充分浸润的外来听者,往往难以准确识别那些细微且重要的声音特征,因为缺少了与当地文化相契合的“文化耳朵”。
只有通过长时间的田野浸润,持续地观察与参与,才能逐渐培养出适应那个文化环境的听觉敏感度与辨识力,才能真正听见、理解并感受到那些声音背后的文化意义和情感表达。换句话说,如何更好地考察唱法?我想,很重要的便是先悬置已有的理论与观念,在长时间的浸润中培养一双新的耳朵。
二、探寻少数民族唱法:
在“科学性”与“表演姿态”中的感悟具身之声
第一天考察时还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我们原计划要前往黑水县采访阿尔麦藏族歌者,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在都江堰市的一个小区中见到了他们。歌者们在现代小区里放声高歌,临近结束时,小区物业人员匆忙地过来告诉我们,许多高层住户频频致电物业,反映外面持续传来很大的声音。

阿尔麦藏族歌者们
听到这一反馈,我们不禁感叹,原来他们的歌声穿透力竟如此强大。这一经历也促使我思考:这些看似天然、随性的声音,是否同样蕴含某种可被辨析的“科学性”?
事实上,这一问题是中国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议题。西方的发声训练方法依托现代生理解剖学,对人体发声器官的结构与工作原理有着清晰且系统地阐释。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的声乐技巧多源于口传心授和个人体悟。但也正如何为先生所言,我们的声乐遗产虽然未以现代科学的语言加以描述,其中却有很多符合声学与生理原理的东西。因此,自以“科学”著称的西洋唱法传入中国以来,学界便不断尝试解析中国声乐的发声机制,为其科学性与合理性提供理论支撑。
此次研修便让我在田野中切身感受到这种“科学性”。阿坝羌族多声部民歌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郎加木与见车牙,两位年逾古稀的歌者嗓音依然洪亮清澈,在演唱以波浪式旋律和大跳为特征的“应毕曼”时从容自如。

阿坝羌族多声部民歌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见车牙(左一)与郎加木(右一)
好的声音背后,往往有一套稳定且合理的发声方式支撑。交谈中我得知,羌族人在日常训练中,第一遍通常小声哼唱,随着遍数增加不断加大音量并带入唱词,这与美声训练中“先通过哼鸣找到鼻咽腔的高位置,再在保持位置的基础上带入唱词”的方法如出一辙。此外,他们常在演唱正式唱词前加一段衬词,以帮助找到理想的发声状态。更重要的是,这些训练方法并非孤立存在于某一少数民族或特定音乐体裁中,而是广泛存在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多个门类中。戏曲长期采用“以曲代工”的练习方式同样如此。由此可见,所谓的“科学性”本就是深植于中国传统音乐实践中的普遍规律。传统声乐中的许多经验技巧,其实是对人体发声机理的长期观察和总结,是与声带振动、气息控制、共鸣调整等科学原理相符的自然结果。
此外,唱法的呈现与传承并不止于声带、喉咙与共鸣腔体的运用,还与歌者的“表演姿态”密不可分。羌族歌手在演唱时,男性常作托腮、摸喉姿势,女性则多叉腰、摸后脑勺或托腮,演唱前还会将唾液抹在喉头润嗓。热务沟藏族女性歌者在演唱“拉依”时,同样会使用托腮的姿势。

热务沟藏族女性歌者们
我初学时曾误以为托腮的动作只是像初学合唱者那样堵住耳朵以防跑调,直到亲身体验后才明白:托住腮部有助于打开牙关、稳定呼吸、控制口咽腔发音,并通过感知口腔开合的幅度与变化,帮助歌者在不同音域中找到准确的咬字与共鸣位置。由此可见,“表演姿态”亦是考察唱法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歌者的身体并非被动执行发声技巧的“工具”,而是承载并传递地方性知识的活态档案。
回望几日的考察,我从初到阿坝时对陌生唱法的茫然,到在一次次具身体验中,真切感受到少数民族唱法的精妙与丰富。六天内所有的理论学习与实地考察,正回应了萧梅老师在开幕式上所强调的“行动力”——唱法研究虽在起步阶段,但研修营已通过交流研讨与田野考察,播撒理念、传递方法,激发起青年学者投身于其中的热情。至少,这颗种子,已在我心中深深扎下根,期待未来的时光里,能够与更多同道中人一同守护、培育与开花结果。

文:孔莹
图:侯赟、孔莹
审核:徐欣、周珂
编辑:鄢杜玖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