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届ICTM专题研讨会“丝绸之路上的鼓与鼓乐”第二、三单元
第二单元:鼓和鼓乐的灵性表达
12月28日下午的第二单元有三位学者发言,由上海音乐学院徐欣副教授主持。

Ako Mashino:
《巴厘岛穆斯林文化中的框架鼓乐团》

第一位发言者是来自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的讲师Ako Mashino。她的发言题目为《巴厘岛穆斯林文化中的框架鼓乐团》(Frame Drum Ensembles in Muslim Balinese Culture)。她以流传于巴厘岛穆斯林社区A、B、C三种类型的框架鼓(Frame drum)及其表演为对象,探索了该地区历史悠久的穆斯林社区所蕴含的宗教文化。
Ako Mashino先概述了自己的田野考察点——穆斯林社区的种族起源与历史背景。其后,她重点讨论了巴厘岛穆斯林社区最典型的三种单面鼓(single-headed drum),以及每种鼓在不同社区中的名称、演奏方式、演奏者性别以及与宗教信仰的关系等,并且与分布在巴厘岛周边几个社区的单面鼓做了比较。
比较结果表明,三种鼓有如下共同特征:其一,三种鼓以穆斯林社区为基础的合奏形式演出;其二,三种鼓以公众庆祝活动的娱乐表演为主,如圣纪节(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先知周年纪念或婚礼;再者,除了B型鼓作为纯器乐演奏,A型和C型为歌唱伴奏。
提问环节:
Aly Abdelaty Ebrahim Hassan(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您刚才提到了qasidah(女声合唱)。就这个词的含义而言,它在阿拉伯语中有“诗”的意思,虽然它可能与“诗”无关。您在论述中提到,没有找到太多材料解释qasidah的来源。对此我想补充一点,在观看视频资料时我觉得qasidah和埃及宗教音乐的合唱形式相似,包括其中用到的乐器。建议您可以关注一下qasidah与中东以及埃及的关系,或许对您的研究有所帮助。
回答:谢谢您的建议。印度尼西亚的qasidah一词原是阿拉伯文中的一种诗歌格律,专指唱词。它与伊斯兰文化相关。我会关注您所说的内容。
Bernard Kleikamp:《热贡扁鼓是萨满鼓吗?——关于萨满教、萨满鼓与击鼓的一些思考》

第二位发言者是来自荷兰的学者Bernard Kleikamp(音乐人类学家、音乐发行人、Pan唱片公司总裁)。他的发言题目为《热贡扁鼓是萨满鼓吗?——关于萨满教、萨满鼓与击鼓的一些思考》(Is the Rebgong Flat Drum a Shaman Drum? Some Thoughts about Shamanism, Shaman Drums, and Drum Playing)。
他于2016 年 2 月 16 日,在青海黄南热贡张家村庙观看了当地萨满祭拉木泽仪式。他先详细描述了祭祀仪式情景以及仪式中的扁鼓(flat drum,当地的羊皮鼓)的形制与特征,并且与社交媒体“快手”视频中看到的与此形制相似的扁鼓相比较。
他认为丝绸之路上的甘肃临夏、陇西、定西以及天水地区流传的扁鼓与热贡扁鼓的不同之处在于鼓尾的形状与金属环。热贡扁鼓的鼓尾没有金属环,属于它的变体。之后,他又以视频形式展示了图瓦共和国的图瓦乐团表演者斯塔斯·丹玛(Stas Danma)于1992年在舞台上模仿的萨满治疗,以及哈卡斯共和国乌尔吉(Ülger)乐团表演的萨满鼓。由此,总结为萨满鼓按照用途具有祭祀与舞台表演两种不同功能。
提问环节:
王晓东(吉林师范大学副教授,上海音乐学院访问学者):根据您的论述,热贡地区的拉哇您称其为萨满,图瓦舞台上表演萨满治疗的表演者也为萨满。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您对萨满是如何界定的?谢谢!
回答:萨满是人与神沟通的中介者,这是学界公认的对萨满的定义。
刘桂腾:
《从聚落仪式的“果若”到公共文化的“夬儒节”——阿坝羌族释比响器配置制度的“非遗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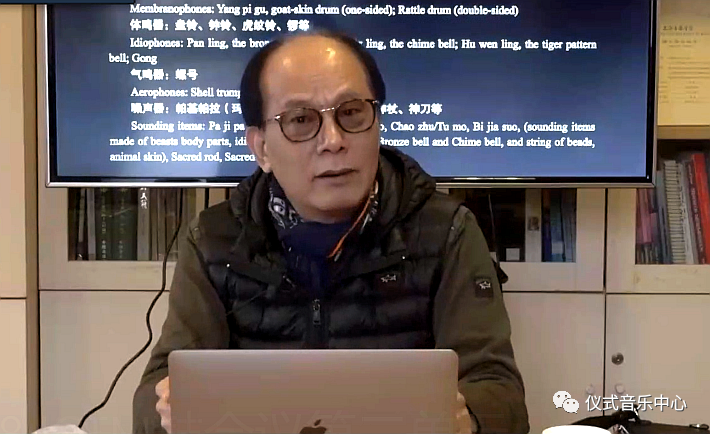
本单元最后一位发言者是刘桂腾教授(上海音乐学院特聘教授)。他发言的题目是《从聚落仪式的“果若”到公共文化的“夬儒节”——阿坝羌族释比响器配置制度的“非遗化”》(Cluster’s“Guo’ruo”Rirual to the “Guai’ru Festival” as Public Culture—The “Intangiblisation” of the Percussion Instrumentation System from the Shi’bi of the Aba Qiang)。
作为酬神还愿、祈丰祛病的尔玛“果若”仪式,至今残留于古羌之地的四川阿坝一带。2018年3月和2019年3月,他带领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阿坝羌族释比响器调查”小组,连续两年先后两度来到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的理县、汶川和茂县进行羌族释比响器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羊皮鼓与盘铃,是羌族释比响器配置制度中的“标配”。当下,这个响器制度的配置模式已经走向“非遗化”,传统的“果若”到现在的“夬儒节”,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反映了时代变革对传统音乐文化形态的深刻影响。
刘教授的发言共分为三个部分。他首先界定了“果若”与释比两个概念。其次,对释比响器中的单面鼓、双面鼓、盘铃、神杖等做了详实的形制描述。之后,他用休溪村传统的“果若”和现在的“夬儒节”两个音乐影像志影片向参会者解读了二者在文化空间、受众群体、文化功能以及响器配置制度的不同之处。他认为传统音乐形态的“非遗化”,是迎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大潮的结果。“果若”释比响器配置制度并未承继到现在的“夬儒节”中,特别是那些具有民间信仰意义的响器等。我们应当承认,利用传统仪式音乐元素进行“文创”是当地人的一种文化选择,因此,我们毋需拒斥作为当代节庆活动的“夬儒节”;但这些由导演编排的文化产品,尽管其中也汲取了传统音乐元素或从传统音乐中获得了某些创作灵感,但它并非“非遗”本身。倘若我们将其视为所谓“被发明的传统”——作为非遗保护的主要途径的结果,必然会毁掉传统音乐长河的水源地。在“非遗化”已成大潮的情势下,对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音乐形态的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正道,是传、承并重,殊途同归——在“保存”的前提下“利用”。重“承”轻“传”,必将付出丧失传统的代价。
提问环节:
Gisa Jahnichen (上海音乐学院全职引进教授):我曾看到有人家里墙上挂着萨满鼓,但他并不是萨满,他所住的村里也没有萨满。这只是他旅游看到买回来的纪念品。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回答:在我们看来这不是一个问题,譬如我们在“果若”仪式中看到的鼓,与在“夬儒节”中使用的鼓的功能完全不同。有的游客把它买回来作为纪念品完全可以,因为二者的用途完全不同。
Tahsin Kuo(线上):面对宗教性的诵唱变为娱乐性的表演,请问当地的执仪人是否愿意看到这种情形发生?
回答:我需要了解当地人的看法,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目前而言还无法代替他们来回答。
第三单元:鼓与鼓乐的流动
第三单元由Gisa Jahnichen教授主持。

本单元共有三位发言者,分别是社会人类学家、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讲师Ulrike Stohrer,柏林洪堡大学民族音乐学教授Jürgen Elsner以及非洲音乐学家Timkehet Teffera。
Ulrike Stohrer:《说话的鼓:作为也门高地非语言交流手段的马法和塔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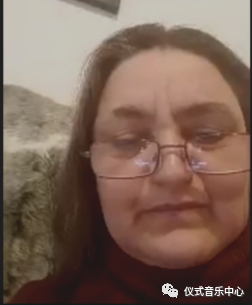
Ulrike Stohrer的发言题目是《说话的鼓:作为也门高地非语言交流手段的马法和塔萨》(Speaking/talking drums: Marfa and Tasah as Means of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in the Highlands of Yemen)。
她主要以两种锅型鼓——马法(marfa’)和塔萨(tasah),来说明在也门高地的部落地区有通过鼓乐来表达的非语言交流系统。也门人没有把这两种锅型鼓归类为乐器,而是将它们定义为仪式的工具。这些锅型鼓有几种节奏,不同的节奏是用不同的声学方式定义公共事务的时间和空间,如婚礼、宗教宴会、部落会议、社群工作项目、客人的接待等。
马法(marfa’)和塔萨(tasah)及其特定节奏,承载着深刻内涵及符号象征性,在也门高地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交流系统。鼓的实体也被看作是酋长的标志,在每个活动中都陪伴着他,并放置在他的睡榻上。所以它们的意义是也门部落生活中一个迷人却鲜为人知的方面,值得更详细地研究。关于也门高地地区鼓的功能及其非语言交流系统,Ulrike Stohrer教授总结如下:为社会事件定义和提供一个和平、受保护的空间和时间;为处于边界的个体提供一个保护性的移动“气泡”/空间;通过典礼和仪式引导个人和族群;充当酋长的徽章,象征着他的力量;为个人、族群和空间标记合法地位、边界和义务;作为任何神圣时间的标志;作为危险情况的警报器。
提问环节:
徐欣(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我想问一个问题,当我们把鼓语看作一种沟通的语言时,不同部落中使用的是同样的鼓语吗?当他们用鼓交流时,他们能明白对方所表达的吗?
回答:是的,这就像一种存在于不同部落之间的交流系统,既存在于部落内部,也在不同部落之间通用。
尹翔(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候选人):您刚才讲述了在不同场合中使用的不同鼓语,不知您可否举例并展示其具体节奏型?
回答:不同场合中鼓的演奏会运用不同的节奏,不同的仪式场合也有其特殊的代表性节奏类型,比如当你听到一个特定的节奏类型时,你就会知道正在举行什么仪式、活动,或者正在传递着什么样的信息。
Gisa Jahnichen:我的问题是鼓手是否被某些富人家庭或者部落长期雇佣?以及鼓手在孩童或者青少年时期是如何习鼓的?
回答:他们过着群居生活,因此鼓的学习是由父亲传给儿子,母亲传给女儿。他们会在一些特定场合表演并获取报酬。比如要举办一场婚礼,就要花钱雇音乐家来表演,如果是社区活动中的音乐表演,就由社区来付给乐手们。
Jürgen Elsner:《也门鼓乐》

第二位发言人——Jürgen Elsner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也门鼓乐》(Drum Playing in Yemen)。
他首先介绍了巴拉舞曲(Bar’a),并说明人声和歌唱虽是也门音乐活动的核心,但人声主导地位的实现方式具有区域差异性,也门音乐的独特性其实是体现在鼓上的。歌唱所使用的节奏元素很多样,并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发展。音调方面也被赋予了更高的优先级。Jürgen Elsner教授以卡马曲的三种节奏为例,说明传统音乐文化的地方性差异。当前城市语境中的艺术音乐节奏的发展按部就班,仅仅依靠打击乐器;与此相比,与舞蹈联系在一起的功能性流行音乐则基于相当复杂的节奏。在旋律上,由独唱、团体演唱或管乐器组成的鼓乐合奏是作曲的基础。按照常规,通常由三到五件乐器组成。根据所使用的鼓的类型创造的节奏,各个地区的合奏团有很大的不同。圆筒鼓是哈德拉玛特的特点。在红海沿岸的低地Tihama,以系绳的大圆筒鼓和深锅型为主;而在高原平原,以扁锅型为主。这些鼓乐合奏的共同之处是在一个宽音高框架(纵向思维)的声音空间。但即使是在地景之内,根据合奏类型、功能、当地或家庭传统,也会产生不同的声音模式。之后,他举例阐述了鼓乐传统中的性别隔离问题,并围绕“音调与功能”“节奏与固定曲目”“鼓乐风格”等展开讨论。鉴于本次研讨会的跨区域导向,他认为把也门鼓的各种类型作为讨论起点也是有意义的。锅型鼓的形制和张紧鼓皮的技术是超越也门本身的。
提问环节:
线上提问(英文):请问在您记写的谱子中,数字代表什么?
回答:以具体数字来表示音的节奏长短,也就是音长。
Ako Mashino(日本东京艺术大学讲师):每个鼓的音高不同吗,有确切的音高吗?还是只是一种高中低音的区分而已?
回答:是不同的,但没有准确测量出来。你确实可以去测一测,但不是很有必要。我想强调的重点是一个鼓与另一个鼓的关系,而不是每个鼓的确切音高。
Timkehet Teffera:《锅形鼓的传播:探索埃塞俄比亚纳加里特鼓的起源》

第三位发言人是Timkehet Teffera博士,她的发言题目是《锅形鼓的传播:探索埃塞俄比亚纳加里特鼓的起源》(Diffusion of Kettledrums: Exploring the Origins of the Ethiopian Negarit)。
那加里特鼓是过去埃塞俄比亚皇室的标志。在伊斯兰世界、高加索地区、中亚和南亚、非洲大部分地区以及欧洲,都采用相似的词汇给鼓命名。这些术语拥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naqqāra, naqqarat, nakkare, negarit, nägära, naker, naghara, nagārā,neger等。这表明了它在世界许多地方传播。这类传播据说是由伊斯兰文化音乐的传播导致的。锅型鼓在世界范围内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是典型的宫廷乐器。它们是国家权力、权威和皇权的象征,在埃塞俄比亚也是如此。如今,它们的使用已大大减少,但至少在埃塞俄比亚正教的Tewahido教堂和修道院中仍能听到它们的声音。除了锣鼓和木梆子外,这种鼓还用于号召会众礼拜,在礼拜仪式和会议以及重大的宗教节日、国家级节日、爱国节日和宫廷的正式和非正式场合中使用。她认为,那加里特鼓并不来自于埃塞俄比亚,因为埃塞俄比亚自古以来就同外部世界,特别是同阿拉伯半岛有着牢固的商业、文化和政治联系。且其论文将更深入地探讨那格里特鼓的可能起源、历史路线、它进入埃塞俄比亚的途径、使用和功能、它过去和今天的作用和它的社会意义。
由于时间限制,Timkehet Teffera博士发言的内容没有提问环节,感兴趣的线上线下的师生们将通过邮件与她取得联系并做进一步探讨。
联合主办:
国际传统音乐学会
上海音乐学院
承办:
上海音乐学院“亚欧音乐研究中心”
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文字:王晓东、林艺婷
审稿:徐欣
图片:王晓东、张珊、张毅
编辑:张毅

b站账号:仪式音乐中心
课程、讲座及工作坊视频持续更新中~
目录:
(1)萧梅《多元文化中的唱法分类体系》
(2)林晨《减字谱中的音乐形态》
(3)萧梅《“谁的呼麦”——亚欧草原寻踪》
(4)宁颖《从朝鲜族“盘索里”表演看“长短”的生成逻辑》
(5) 崔晓娜《从音乐实践看“旋宫不转调”——以河北“十番乐”为例》
(6) 萧梅 《多元文化中的歌唱方法与表演专题》第一课
(7) 萧梅 《萨满(巫)仪式音乐中的“制度性展演”》
(8) 杨玉成 《传统音乐的“逆向”重建——以蒙古族科尔沁英雄史诗的活化演唱实验为例》
(9)粤东海丰陶塘(下元节)礼俗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