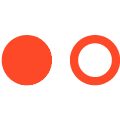(2020年4月)徐欣 | 聆听与发声:唐·伊德的声音现象学

【作者】徐欣(1981-),女,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本文为作者在上海音乐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写作的阅读报告(导师:萧梅教授)。文章发表于《音乐研究》2011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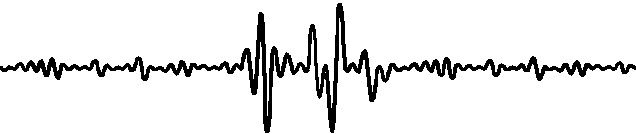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充斥着音响。这些音响,有些被结构化为语言和音乐,有着不同文化所属的固定语汇与表达方式,有些看似零散、偶然,来自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有这一切,令我们的世界成为一个巨大的发声体。那么,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中,声音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它对于我们认识世界与生活又有着何等意义?进而,我们又能以何方式去发现这种意义?如此种种,是唐·伊德(Don Idhe)在其《聆听与发声——声音的现象学》一书中试图阐明的问题。
唐·伊德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以技术现象学的研究而著称。虽然他所专注的技术哲学与海德格尔的开启相关,但伊德认为,尽管为技术哲学引入现象学方法是海德格尔对此领域的最大贡献,但他同时却忽视了技术与知觉关系的维度。由此,伊德对知觉在人的存在中的重要性给予了极大的肯定与论述,这本专注于“声音”与“听觉”的著作,即为他所阐发的知觉与人的存在经验之认识。该著由作者在其1976年撰写的第一版基础上扩充了七个章节后再次出版(Don Idhe:Listening and Voice: Phenomenologies of Sound, 2ed. editio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正如他本人在第二版序言中所说,这些扩充的观点与论题是他专注于“听觉体验”多年的持续研究成果。在全书六大部分共二十三章中,作者始终围绕着“现象学地认识‘聆听’与‘发声’”展开。
第一部分为导论,伊德在此首先为声音研究定位,并在与西方视觉中心主义的比较、反思中确立了声音研究的合法性。他认为,视觉中心主义是思想史的症结,它主导了我们关于现实和体验的思维,而“声音”的侵入则揭示出一些我们认识世界的视觉方法,即“世界观”(worldview)中尚未被关注到的重要内容。其次,他对现象学传统中的相关概念、人物做了背景式的陈述,其中包括对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等人现象学思想的梳理。秉持“将一切事物悬置判断”的现象学态度,伊德将声音研究的方向回归至声音本身的发声与聆听上,在现象学的认识框架与术语体系下分析并阐释了声音的特质及其与人的知觉之关系。该书的第二部分为现象描述,包括以下内容:听觉的维度;声音的形状;听觉场(the auditory field);声音的时间性(timeful sound);听觉视域(auditory horizons)。第三部分为“意象模式”,主要探讨的是人的听觉意象。作者从这一层面讨论了声音的两个属性:一种是实际听到的声音,另一种是想象的声音,即人们不仅仅听到世界,也听到了自己。伊德将其形象地称为“体验的多声部”。以上三个部分,是伊德对于“聆听”的集中论述,他令我们以各种方式“听到了”声音所传达的意义,这种意义可能来自声音本身,也可能来自声音场域与环境,亦可能来自于人的内在听觉意象。
从第四部分开始,伊德转向对于“发声”的探讨。voice一词在英文当中有专指“人声”之意。而伊德将所有的声音(sound)都理解为发声(voice),无论声音的来源是物体、他者、人,还是神。之所以做如是宽泛的定义,是因为voice是富于意义的,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声音”。伊德以广义的“voice”批判、或者说超越了将声音化约为纯粹的音响,或仅仅局限于脱离情景的抽象聆听的声音观念,而这些声音与聆听的观念,显然是无法听到“voice”所揭示出的“他者”的。伊德以“现象学”命名了该书的第五部分,进一步对“发声的现象学”、“听觉意象”、“聆听”进行了细致的现象学分析。在最后的第六部分,作者讨论的是听觉技术。如果将全书视作唐·伊德对于现象学传统的延续,那么他在此处所涉及到的对于技术哲学的思考,并将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与“技术哲学”相结合,将技术的扩展与人的知觉扩展视作一种同构关系,则可以说实现了对于现象学、乃至于技术现象学的超越。
正是在以“体验”为论述目的关照下,伊德以自己的听觉体验及描述,构筑了整部著作的民族志材料。可以说,该书完全建立在他本人的聆听历程、感官认知及其反思之上。其第一人称的写作策略使人们在阅读时仿佛不断与作者进行密切的对话,这很容易唤起读者对于类似的自我听觉体验的回想。我们可以将这种“自传体”式的写作视为他对“聆听本体论”的一次实践。在阐述视觉与听觉的不同边界时,他写道:“我沿着一条黑暗的乡间小径行走,几乎看不清道路的轮廓。在探索中,我敏锐地注意到了各种声响。突然间,我听到了猫头鹰的尖叫,这叫声仿佛被黑暗放大,震颤了我的身体,但是却看不见这只鸟在何处。”(同上,第51页。)在对声音的时间属性与空间属性关系的论述中,他启用了大量的主观描述:“我闭上眼睛,注意到一个声音接一个声音的出现,一个单独的声响‘存在’一段时间之后随即逝去;声音的时间领域是有持续性的,时间的浪潮戏剧性地不断展现。”(同上,第57页。)“我不仅能听到台球在桌面上滚动的圆的形状,也能够听出桌面的硬度。”(同上,第67页。)“我去听音乐会,交响乐队在前方演奏。突然,整个大厅被音乐填满了……此时此刻,这个开放的空间被瞬间完全的呈现出来,声音的丰富性压倒了我们对于物体和方向的一般看法……当音乐从前方倾斜下来,我将头转向一边,猛然,我戏剧性地听到回声潜藏在离我很远的地方,仿佛交响乐队包裹着我。在回声中,我听到了整个演奏大厅的内部结构。聆听带来了空间上的意义。”(同上,第71页。)等等。如同声音的绵延和叙事的特性,在唐·伊德的写作中,其对每一个理论问题的揭示,必然来自于一段或几段生动的个人体验。我们在这种表达框架之下,能够真切地发现感性与理性、体验与阐释是如何凝聚在一起,并共同建构了声音现象学。
“体验”与“缘身性”(embodiment)(萧梅在相关文章中曾谈到,关于“embodiment”在国内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用法,比如“具体落实”、“具身化”、“体现”等等。其中,“体现”是最常见的译法。科学哲学研究学者根据该术语在当代的研究主题,运用内涵及其与哲学的渊源,采用了“缘身性”这名称。她对这一译法给予认同并采借,希望以“缘身而现”的提法来强调“那种身体体验在境域中重重缘发,相互指引的过程及其某一‘缘在’。”详见萧梅《“缘身而现”:迷幻中的仪式音声》,曹本冶主编《仪式音声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322页。)是一对无法分割的概念。人对于声音的体验,并非单向度的作用于听觉,而往往是以整个身体来感知音乐。声音的“缘身而现”是伊德在“听觉意象”所重点提及的内容。他列举了民间音乐的听众是如何用腹部与脚来“听”低沉的贝司声,聋哑儿童又如何以手及手指来学习“听”音乐。此外,在该书的重点部分,即在对于声音现象的描述中,他以音乐所具有的“渗透力”,诠释了音乐的缘身性特质:“声音物理性地穿透我的身体,我以我之身躯,从骨头到耳朵,‘听’到了它。”(Don Idhe:Listening and Voice: Phenomenologies of Sound, 2ed. editio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p. 81.)伊德强调,必须要将感官间的区隔替换为总体经验上的“相对焦点”,而纯粹的基于单一感官的体验是不存在的。原初的东西在朴素的体验中总是被“合成”的。实际上,缘身性是探讨声音体验的思想基础,身体的综合感觉,作为听觉主体与世界交互关系的重要环节,是伊德讨论听觉体验的一项重要参数。
正是因为音乐是一种高度结构化,并极富标识性的声音形式,所以它亦自然成为伊德讨论发声与聆听、以及听觉体验与“技术化声音”的一大主题。在全书各处,他都穿插了以音乐为对象的现象学阐释,并涉及到了音乐在听觉体验上的特质、缘身性与音乐聆听、听觉场中的音乐之声,技术工具与音乐等等。伊德从现象学出发,认为音乐以其自身而呈现(The music presents itself),这推动了我们以新的视角重新认识音乐;而音乐学家们则以现象学的方式来解决音乐难题。作为理论学科,音乐学所面临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在于如何通过非音乐的文字语言去描写表述文字语言所不能表达的东西。英国学者马丁·克莱顿(Martin Clayton)认为,关注人类体验和阐释声音的方式,是连接音乐体验和非音乐表达之间存在的距离之途径。他寄期望于以听觉体验的方式改变以往仅仅以文字来转述音乐的情形,而将对于音乐意义的获取回归至人们的音乐感性经验。(Martin Clayton, “Toward an ethnomusicology of sound experience”, Stobart, Henry ed. The New (Ethno)musicologies. Lanham, MA: Scarecrow Press, pp. 135–169)同样,面对查尔斯·西格(Charles Seeger)一生所纠缠的“语言如何言说音乐”的困境,中国学者萧梅设问到:“如何真正运用一种提炼的、定义的语言去表达音乐的知识?”“音乐学是无可奈何抑或充满挑战”?(萧梅《回到“声音”并自行敞开》,《音乐艺术》2011年第1期,第79页。)她强调,沿着音响现象还原的思路回归声音,学习聆听,既能够使学科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困境,亦可作为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策略,以音乐学本位为立足点而展开文化中的声音意义之探索。
作为一名技术现象学家,唐·伊德在第六部分集中探讨了“工具”在我们听觉体验中所扮演的角色。现代化的技术工具,如电话、广播等等都扩展了我们的听力,同时也使得声音渗透至我们的生活,就像在起居室里听到从音箱中传来的披头士或者贝多芬的音乐一样。最重要的是,电子化的交流使我们注意到,曾经“寂静”的领域,实际上充满噪音与声响。通过电子扩音设备,我们可以听到海洋中回荡着的鲸鱼的歌声和虾的打击乐。与此同时,噪音污染亦充斥着我们的城市,威胁着我们心灵的宁静,并使我们向往着安静的时代。
从伊德的观点来看,这不仅仅是由于技术使世界突然变得嘈杂了,也不仅仅是我们因此而听到更多,或者是声音本身一不留神就渗透了技术化的文化。这实际上反映出我们这个充斥着电子仪器制造的环境和时代技术的发展所导致的听觉体验与听觉能力的重大变革!正因为这一变革,我们比以前的任何一代人都能听的更远;并亦在这听觉体验和听觉能力的变革中,改变了我们对于世界和自己的看法。
此外,伊德还关注到科学工具与音乐知识生产方面的不同:科学工具总是产生视觉上的结果,或者是产生出新的工具;而音乐总是利用工具来生产声音。在音乐与工具这一对关系当中,有些人是传统的忠实拥护者,他们不但不会为新工具的诞生而兴奋,相反却倾向于旧工具的使用,伊德将此视为对于新工具的反抗。这就是他在第六部分“从巴赫到摇滚”章节中主要涉及的内容。随后,作者又从摇滚转向爵士乐,讨论了作为新发明的电子萨克斯在爵士乐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在“缘身性:科技与音乐”章节中,他直接介入更为现代化的乐器,包括电子乐器与合成音乐对于人的知觉扩展。在这部分的末尾,伊德还关注到对于听觉“义体”科技的体验。他从自己佩戴助听器的经验指出,我们发明了工具,但是工具亦“重新发明”(re-invent)了我们自身。工具在与我们的知觉体验发生交往的过程中,成为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的知觉在工具的辅助之下得到了延伸。在此,我们不免联想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第128页。)所揭示的人与世界之关系。伊德还评估了科技对于音乐的影响力,他认为,技术与工具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电子的革命带来了声音的再生产,尽管电子技术呈现的音响无法与现场聆听保持绝对一致,但这种技术使“听音乐”变得更加容易,也离我们的生活更近;此外,科技亦有意地改变着声音本来的样子。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子音乐无疑是对声音形态及其可能性的无限开拓与发明,它将过去从未存在的声音带入了我们的听觉世界。
唐·伊德的声音现象学研究,是近几十年来逐步形成的听觉文化研究话语谱系中的一员。在西方,雷蒙德·默里·舍费尔(Raymond Murray Schafer)自上世纪60年代起,以他的“音景”(soundscape)以及“音响生态”(acoustic ecology)的相关理论与研究计划,首次将对于听觉与声音环境的考察作为衡量人与世界关系的重要内容,为“听觉”与“声音”开辟出崭新而广阔的话语空间。与“soundscape”中所流露出的将听觉文化空间化的意图相呼应,在传媒与现代文化领域做出贡献的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亦提出“听觉空间”(acoustic space)的概念,认为声音既有时间属性,也有空间属性。在面对现代文化中媒体技术的影响时,他认为,媒介不是冷冰冰的外在化的存在,媒介就是人的身体、精神、感觉的延伸。媒介改变了人的存在方式,重建了人的感觉方式和对待世界的态度。伊德的“技术现象学”无疑与其形成了相交和支撑。尽管具体的领域和探讨方式呈现多元化,但从麦克卢汉、舍费尔以及唐·伊德的“声音视域”中,我们能够非常清晰地捕捉到他们对于现代文化空间中的声音和听觉变迁“究竟处于何等关系”的共同追问。
声音在变,声音现象学的领域也在不断变化着。根据伊德的介绍,近年来,学者们将这一领域朝向更为丰富的方向不断开掘,新的认识与观念不断涌现:有学者关注到交流理论中的听觉本体论,以发声(voice)的具体性和实在性平衡了目前一些起主导作用的抽象理论;一些学者将音乐的对象视觉化,并直接影响和关涉到记谱的新模式及其对音乐学的重要意义。还有学者发展出新的脱生自科学研究的“声音研究”分析方法。不过,无论这一领域以怎样的方式更新发展,它都持续地以自己的方式提醒我们,声音的意义在聆听中自行敞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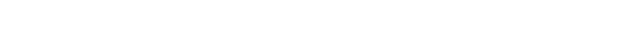
总策划:萧梅
文字:徐欣
编辑:尹翔
【声音研究专题】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