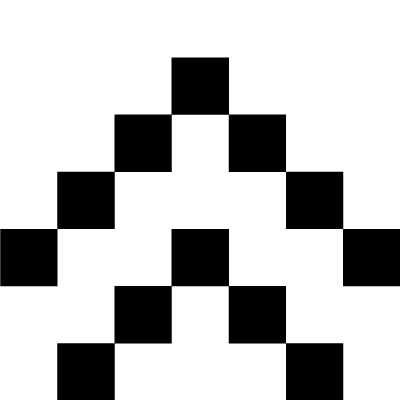(2020年4月)声音材质、皮和骨:欧亚商贸之路上的鲁特与生态
作者简介
声音材质、皮和骨:
欧亚商贸之路上的鲁特与生态
JENNIFER C. POST
邓晓彬 译 萧梅 校
对于那些研究乐器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运用情况的学者,他们可以提供对乐器的描述性信息,如在某个具体时期或地方的使用情况。有些学者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乐器承载了社会和文化意义,体现了当地价值观和国家价值观,呈现了一个社区的经济状况,连接了本土的信仰,也展现了独特的风格或技法[民族音乐学者自20世纪中期以来就展示了这种乐器研究的方法,见达维(Dawe,2011)有关乐器的文化研究的出色概述]。然而,以往的乐器研究往往忽略了乐器在完全成型之前的重要的历史阶段。在那个时期,制作者会选择木头、皮或其他材料来做成发声的物件[可参考引用更为广泛的资料,如梅里亚姆(Alan Marriam)关于Bala鼓制作的文章以及笔者对布莱金(Blacking)关于乐器制作文章的讨论 (Merriam 1969; Post 2015)]。实际上,乐器的制作都会经历从确认制作材料、培育到准备使用的过程。乐器制作者常常会忘记制作材料与乐器制作的社会文化系统间的社会关系(Bates 2012; Roda 2013)。他们根据自己对木头、皮、骨以及其他能发出声响的物体的丰富认知,并运用特定的技能和制作方法,确保所制作的乐器能够得到本土音乐家们在音乐和审美上的认同。正如库雷希(Qureshi)所说,乐器会说故事,因为制作乐器所用的材料、状况以及设计是历史实践和现代变化的证明(Qureshi 2000)[见兰瑟(Rancier)2014年对库莱希(Quereshi)方法的运用]。选择使用木头、皮还是其他材料以及制作者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情况都会包含在每件完整的乐器中,因为这些社会的、生物的和文化因素会控制着整个制作过程。其中一些最重要的因素包括基于历史的先例、土壤的健康状况及其产品、获得所需材料的途径以及制作者的聪明才智。
本文重点阐述特定的欧亚地区长颈鲁特(long-necked plucked lute)的制作和材料,以及它与商贸之路的历史关系。本文为一个更大项目的组成部分,项目的目标是探索材料在音乐制作悠长且复杂的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特别是那些制作者将其转化为音乐和审美俱佳的乐器制作材料的自然资源。笔者在文中探讨了早期商贸之路上材料的传播以及随着时间的流逝,制作乐器的材料价值和使用。探讨的过程中考虑了生态和社会经济变化对乐器制作的影响并分享了改编和创新在变化中所起的主要作用。笔者着重联系了早期丝绸之路环境中不可避免的生物和文化变化以及今天丝绸之路环境中的相应变化,其中会探索人与环境的互动,涉及景观生态学和生态文化多样性等学科内容。这些学术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历史背景来理解长颈鲁特及其他乐器制作实践的变化。随着时间的迁移,生态和社会因素会影响人与环境的互动。这些生态和社会因素的关系包括对重要的人类和非人类关系的认可、自然资源管理状态、森林体系以及植物和动物的健康等。笔者的信息来源包括对特定乐器和乐器类型的民族音乐和形态研究、特定材料的共鸣的音乐信息,研究欧亚生物多样性和环境变化的科学家的生态数据以及笔者在2004至2015年间于东亚和中亚部分地区进行实地研究的资料。
在欧亚地区的大部分地方,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制作长颈鲁特的材料取自于多种多样的自然资源,包括高价值的木材、动物的器官(胃、心脏、肠)、皮、骨、角、壳、动物胶以及用于制作弦的金属[近年来,其中一些材料替换为合成材料和复合材料,如用尼龙制作弦,用合成胶和塑料做琴码和装饰]。乐器木料(共鸣板)、经加工的动物皮、鱼、爬行动物和其他材料被高效并集中地运用在了家庭传承,或是通过对古老乐器的研究所习得的制法当中,制作者认为这样能展现出一种传统上的延续性。通过与中国、蒙古、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耳其的乐器制作者交流,笔者发现大部分制作者都希望能保留早期传承的工艺和材料。与此同时,他们创新设计,根据可用的资源对结构进行改善和提升。虽然方法不同,但通过稳定的材料供应以及稳定的音乐和审美质量保证了始终如一的体系。乐器制作主要保留在中亚和东亚。数百年来,人和动物走过了商贸之路[此句内在的含义认为人类行为对扩散过程起了一定的作用。人类行为多种多样,有生物成因,也有地质学的成因],他们所经过的地方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其中大部分地区也经历了多个世纪时间流逝所带来的生态和政治压力及变化。
材料的传播和文化实践
为了能够更全面地理解物体的流动性及其对乐器制作产生的影响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了解植物的传播等方式展开研究。了解植物物种需要考虑植物的分布和进化,尤其是在新兴的植物生物文化多样性领域中进行探索,采取整合性的综合研究,区分特定的族群(以及他们的文化活动,包括语言、生活习惯、食物和艺术表达)以及植物传播和管理实践(参见Pollegioin等 2015)。
实际上,木材及其他制作乐器的材料可以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并结合地形、气候和人类贸易等要素进行分析。在很多不同地方,随着商贸之路而移动的动物、种子和植物对于乐器制作材料的选择和价值分析大有作用。对于某些资源而言,商贸之路是他们的“基因走廊”。在亚洲,从早期青铜器时代开始[瓦赫达提(2014)指出,在亚美尼亚南部,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谷地和中国东北部的河北省都有发现],胡桃树就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大量科学家在数条商贸之路发现了胡桃树(瓦赫达提/Vahdati 2014)。珀利杰尼(Pollegioni)认为胡桃树在中亚同时开始生长,从新疆到高加索地区都有;与此同时,由于人类的管理和开发利用,其他果树和物种也在传播和进化。人类的管理和开发利用包括人为传播、人类的文化交流以及植树造林(参见Pollegioni等2015:1)[珀利杰尼勾勒出移动路径并找出了与人类移动相应的四个不同种类的树,商贸之路上的主要交叉口以及语系。他指出语言证据(与其他证据相比)可以用于寻找类似品种的树木。他说:“民族语言的障碍反映了众多人类社区的文化差异,也影响了基因结构”(Pollegioin 2015:3)]。科学家发现胡桃树集中在早期的商贸之路和贸易中心,展现了胡桃树沿着这些路径的历史传播。
其他具有区域价值的树木如杏树和桑树,他们的种子和幼苗也随着商贸之路进行传播(伍德/Wood 2002; 奥拜勒/Aubaile 2012)。人类和非人类的关系对社会、经济和生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养蚕业的传播(从第2到第7世纪之间开始)以及桑树对丝绸生产的作用(因为幼蚕主要进食桑叶)是展现人类和非人类实体关系的众多例子之一。就桑树而言,幼蚕是牲畜的食物,桑树的果实和叶子则可以用药,树干可以用于造纸。[同样的,红杉也有很多用途。红杉是一种绿荫树,可用于制作家具、雕刻,在印度还用于制作乐器。红杉的花产生一种黄色粉末,树干可以修复伤口,树脂可用于退烧]同样的,杏树如其他核果类树木一样,随着丝绸之路的运输,在中国和中亚之间移动。这些树木的果实和木材也得到了运用(Aubaile 2012; 菲德盖利/Fideghelli和恩格尔/Engel 2014)。核桃树、杏树和桑树这三种树木、丝绸以及动物维持了商人和那些安定下来的人的生计,也在横跨日本到土耳其的数个世纪的乐器制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韩国和日本,阿塞拜疆、土耳其以及西亚其他国家,桑树用于制作乐器]与商贸之路有关的皮、骨和其他材料不仅是因为人类和人类的商品的移动,更是因为动物和植物沿着同样路线的移动(如附于动物皮毛上)。在很多情况下,动物和植物的移动比人类的移动要早好几个世纪。
乐器木料
如今,选择用于制作长颈鲁特的木材受历史使用、制作者和音乐家的经济情况、气候以及气候变化等影响。早期商贸之路的旅途会影响历史使用,包括木材可用性的变化以及新引进的木材。
在安土重迁的地方,大部分制作者使用杏树、桑树、胡桃树和梨树等果树,而在北方或者纬度高的地方,由于频繁迁徙的游牧民族长期居住在那里,则较多使用软木如杉树、冷杉、松树和云杉以及生长迅速的硬木如桦树和白杨。尽管较难从可靠的历史文献中找出可以证明生活方式以及乐器制作材料的有力证据,但历史表明,随着商贸之路移动的树木为安土重迁的地区的制作者提供了可以使用并可以长久使用特定果木制作当地乐器的机会。简而言之,游牧民族从临近的森林(松树、冷杉)或者湿地(桦树、白杨树、柳树)寻找当地的木材制作乐器,而定居民族则持续地使用商贸之路所带来的木材。
在亚洲,长颈鲁特制作者对用于制作乐器的材质、共鸣箱、琴颈和其他部件的木材有着非常高的标准。大部分制作者认为,最理想的木材是原始森林里的老树。只有从这些老树上取得的木材才有最佳的密度和如一的弹性。这些树木的年轮间隔一致,意味着它们在理想的气候环境中成长。关于木材的质量、密度和韧性[在布哈拉(Bukhara)和希瓦,二十一世纪的制作者区分了不同种类的桑树,指出不同种类的桑树特点不同。日本桑树的木质优良,阿塞拜疆桑树的优点则在于韧性],制作者也表示希望使用没有瑕疵的木材,如没有节瘤(虽然在如今的生态环境中难以满足这样的要求)。[年轮可以展现树木成长过程中的历史和森林的健康度]他们也表示考虑到审美和音乐等因素,虽然会对用于不同质量的乐器的木材作区分(因音乐家不同的表演能力和经济状况而定),也会拒绝使用一些木材。[极少欧亚国家还保留有原始森林。但制作者对寻找一套稳定质量的模型表明,虽然他们不能获得这些材料,但他们明白最优资源和最佳实践的重要性]在特定商贸之路地区之外的制琴师因认可云杉高共鸣的价值,用云杉木制作共鸣板。[在欧美地区,结合软木和硬木制作的乐器非常常见,制作的乐器包括小提琴等。在欧亚,哈萨克的冬不拉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考姆兹(komuz)如今也使用软硬木结合的方法]然而,从伊朗横跨到中国的制琴师仍然认为白桑树、杏树和胡桃树是用于制作长颈鲁特(和其他乐器)的最佳材料之一。实际上,布雷默德(Bremaud 2012)和吉川(Yoshikawa 2007)分别指出云杉等音乐性能评价高的木材在这些地区的价值并没有这么高,使用也没有这么广泛。贝利(Baily 1976)、 斯洛宾(Slobin1977)、 迪兰(During 2012)和坂田(Sakata 1980)等认为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伊朗西部和乌兹别克斯坦,从二十世纪中期到末期,共鸣板一直都是用桑树制作(在可能得到的情况下),其他部件则用杏树和胡桃树制作。[在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和伊朗部分地区(Slobin 1976; Sakata 1980; Baily 1987; During 2012; Wong 2012),白桑树、杏树和胡桃树被认为是制作乐器的最佳木材,特别是(但并非绝对)弹拨鲁特和弓弦鲁特]在2008年和2009年间,我在塔什干,从默罕默德纳兹·尤索夫(Muhammadnazir Yunusov)处得知他一般会结合使用桑树、杏树和胡桃树制作他的长颈鲁特,布哈拉的制琴师德康(Dekhon)和奥塔别克(Otabek)也是如此。[在此感谢亚历山大·朱马耶夫(Alexander Djumaev)。他为我在2008和2009年间在乌兹别克斯坦与制琴师的工作提供了重要帮助]在众多塔尔(tar)制作者中,希瓦(Khiva)的制作大师奥佐德胡詹尼奥佐夫(Ozod Hujaniyozov)和古迪耶萨拉耶夫(Qodyr Salaev)也结合使用桑树和杏树。值得注意的是,与云杉相比,桑木的弹性和损耗较低,对制作乐器来说,共鸣会稍弱一些。然而,在吉尔吉斯斯坦,马拉贝克-贝里克巴夫(Maratbek Berikbaev)和纳马茨别克乌拉利耶夫(Namazbek Uraliev)用杏树制作考姆孜(qomuz),用当地的云杉做共鸣板。[在此感谢亚历山大·朱马耶夫。他为我在吉尔吉斯坦与制琴师的工作提供了帮助]我在拜访一些制琴师后,发现他们不仅注重木材的选择,也表示对木材年龄的关注。因此,他们的工作室里可以看到很多做了一半的乐器放在墙边或者叠放在木架上,等着木材慢慢变老。
在乐器制作过程中,只有一些木材被认为是坚硬、密实、有共鸣并且达到美观要求的。在这些要求中,共鸣是最重要的。但根据研究和制琴师的经验表明,选择用哪些材料制作鲁特并不一定只看共鸣,美观因素也非常重要。在对小提琴用料的研究中,布雷默德表示“质量等级并不是与音乐性能有关,更多的是物理和视觉要求”(2011:2014)。在对商贸之路所经地区的观察中,我发现制琴师可以根据想要的木材调整结构。制琴师可以通过调整结构的方法来改变一块质量平平的木材的音质(包括板的厚度)。布雷默德说:“制琴师一般认为他们可以用质量中等的木材制作一把好的小提琴,但用质量差的木材就不行了”(引自同书)。在欧亚地区,制琴师调整那些价值得到肯定而且可用的木材以保持音乐的延续性。
皮和骨
在欧亚,多种皮被运用于长颈鲁特的鞔皮(sound table)。皮的选择与地区、生活风格和当地风俗有关。同样的,在不同的地区和景观中,骨、壳和角的使用也有所不同。从研究角度来说,研究皮的历史使用比木材更为困难,因为皮更容易损坏,较少匠人考察皮而且几乎没有科研项目研究本土皮的使用。尽管有关于土耳其和中国地区用壳制作装饰品的大量资料,但我们几乎没有找到与乐器相关的骨和壳的资料。提供了木材使用细节的民族音乐学者通常较少给出有关被沿用已久的乐器制作材料的具体信息[斯洛宾在他对阿富汗北部广泛的音乐研究中,简单提到了骆驼、牛和羊骨(1976)]。例如在描述1950年演奏都塔尔(dutar)的时候,贝利说,“主体是从一块桑木中刻出来的,面板是由同一材料的一块薄板中制作而成。琴颈由桑木、杏木或者胡桃木制作而成。指板嵌入钻石状的小块骨头,面板的周边用同一材料的长条状做装饰,内部嵌入了一串短的骨条。(Baily 1976:31)”
在某种程度上,关于皮和骨研究的有限资料反映出了制琴师的价值。我在采访过的制琴师中发现,他们很乐意去讲述他们使用的不同种类、不同质量的桑树,或者表达他们希望获得哪些木材的愿望;但他们只有被问到的时候,才会讲讲使用的不同类型的皮、骨或壳。
在博物馆可以寻找到长颈鲁特鞔皮的皮材。通过与制琴师的交流,我收集了关于鞔皮的资料。这些资料显示出对皮材的选择往往和获得材料的难易程度有关系,同时也与制作者是否愿意使用不同的皮材有关。不同的皮材应用在长颈鲁特上会对声音产生重要影响,通过追溯这些变化,可以发现人和动物的流动以及土地的肥沃程度。除了哺乳动物(部分地区用家禽的皮制琴,包括羊、牛、骆驼和驴),我们发现特定地区也有使用爬行动物(特别是蛇)和鱼用于制作长颈鲁特的鞔皮。由于家畜组成的变化,用于制作鞔皮的家畜也会发生变化。用不同的皮制作长颈鲁特意味着声音不同,如蟒蛇皮和牛皮的音色就很不一样。如果乐器用料的变化取决于能获得什么样的材料,那么这一变化的历史过程也可能会被看作在变迁的声音、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对音质的一种审美上的偏爱。
用蛇皮制琴,与贸易、乐器的区域间流动以及声音和美感的价值紧密相关,在东亚地区尤其如此。有资料显示,在中国唐代(618-907)蛇皮用于制作忽雷(琵琶的前身,呈梨形状),据说是从中亚乐器衍生而来(展安伦 2000)[展安伦(Thrasher)认为用蛇皮包裹的忽雷和火不思都是由中亚的鲁特衍生而来(展安伦 2000:57)]。在十六世纪,蛇皮及其声音从中国传播到冲绳。冲绳的三线(sanshin)以中国的弹拨三弦为原型。关于弹拨三弦的记录最早出现在元朝(展安伦 2000:51)。制琴师希望找到蟒蛇皮制作鞔皮,但因为当地没有,所以要从东南亚进口。当乐器传播到日本后,人们改用哺乳动物的皮来制作三味线(shamisen)。[现在也跨越了国界]蟒蛇皮(以及羊皮)用在蒙古的三弦长颈乐器“舒达拉嘎”(shudraga)最早出现在十五世纪(马尔什/Marsh 1990:20)。在中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这种声音也被应用在维吾尔族的热瓦普中(还有他们的达卜手鼓)(王/Wong 2012)。到了二十一世纪,由于蟒蛇在部分地区被认为是濒危爬行动物,所以蟒蛇皮的使用被严格监管,这可能会对未来用蟒蛇皮制琴产生一定影响。正如桑树一般,使用蟒蛇皮制作乐器反映了社会、文化和政治交互关系对乐器制作的影响。
用鱼皮制作鞔皮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亚和西亚,遍布于这两个地区的弦乐器(如伊朗的卡曼恰(kamancheh),土库曼的基恰克(ghichak)和伊拉克的交兹(joze)既使用鱼皮,也用绵羊皮或其他柔软的哺乳动物皮,应用于它们相对较小的共鸣箱。伊朗的大型双音箱塔尔琴(double-chambered tar)会使用鱼皮或者哺乳动物包裹心脏的薄膜制作,而源自伊朗和阿塞拜疆同类乐器的乌兹别克弹拨鲁巴布(rubob)和塔尔琴有时候也会使用同样的材料。
现在的乐器作坊用塑料代替了骨和贝壳,用于制作琴桥、弦轴、拨子、音柱(posts)、音梁(ribs)和装饰镶嵌,起着美观与标志乐器类型及制作者身份的双重作用。[塑料也得到广泛应用]乐器的镶嵌材料的变迁、地方性的设计样式乃至各地区不同设计之间的关系值得深入探讨。斯洛宾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对这方面进行探讨,但并没有继续下去(Slobin 1976)。斯洛宾认为,他所见过的很多样式,在空间流布上是非常广泛的。他说:“似乎没有强烈的理由可以把这样的设计单单与中亚匠人联系起来,因为类似的装饰在伊朗以及阿富汗的帕什通也有。”(引自同书:240)这个观点也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讨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以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分析镶嵌物和装饰性(或功能性)的部件(如琴码),以展现不同的历史关系并呈现经济(和生态)模式。阿卜杜勒·卡罕·卡拉赫(Abdul Kahan Qalakh)是新疆东部的一名制琴师,他给我展示了用骆驼骨和牛骨细心制作的镶嵌物。他说,即便身处二十一世纪,他也从健康的角度考虑而不计成本,绝不使用塑料。在新疆和蒙古,装饰物和雕刻等设计已被纸和绘画所替代,这样既能标志制琴师和乐器的身份,也可以保证较低的生产成本。
适应和创新
欧亚地区使用自然资源制作长颈鲁特的做法启发我们去发现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历史中的重要资讯,也包括了这些信息中体现出的适应性。虽然木材、皮和其他材料的共鸣对于制琴师和音乐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但也有资料显示,在乐器制作过程中也有其他同样重要的因素。当中的一些因素显现在制琴师与所用的植物或动物的关系与评价,以及他们对资源质量和渠道等难以避免产生的变化之应对。如今,气候变化和土地管理问题对森林土壤贫瘠、水资源和牧场造成的影响意味着欧亚地区乐器制作的未来也不乐观。制琴师的行为以及选择的材料说明,人们可以通过适应和顺应的方式来应对。其具体方法包括:建立与高级材料的联系、保持对结构性特点的深度理解以帮助思考如何使用和应对气候和社会经济变化,分析不同尺度的变量因素,展现所使用材料的灵活性以及知识创新,从而达到管理变化和改进方法以及最终产品的目的。
我们找到把握变化的不同方法,这些行为最终对每个地方的乐器质量和声音产生影响。乐器制作的灵活性展现了当木材或其他资源的质量没有达到最佳状态时,人类调整自我适应环境的意愿。制琴师通过调整设计以及创新来发挥他们可获得的材料的最大效用以及支撑音乐家的需要。在那些因土地退化、森林使用限制以及经济条件不许可等因素而影响生产的地区,我见证过这些适应性行为。2006年,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扎克塞利克(Zhaqsylyq)把同一颗云杉上的枝条靠近耳朵并且敲动,以判断当冬不拉的音板组装好以后,这些云山枝条是否会产生共鸣。他还说,如果其中一个枝条与其他的不和谐,那么全部都不能用。在蒙古的一家工作室里,麦迪汗特(Medikhat)也用同样的方法去听他那用当地松木做的音板;在喀什,莫米特-伊明(Momet Imin)在做都塔尔的音板的时候,也对一块桑木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在蒙古西部和中国西部地方的制琴师,由于生意压力大,如果有一块木的声音与其他的不协调,他们为了完成制作,愿意用另外一棵树的一块木来替换。当古老木材不可用的时候,回收的木材如屋子的大梁、老桌子或老椅子也可能会被使用。多兰(Dolan)是在麦盖提(Mekti)以外的一位卡龙和热瓦普制琴师,阿卜杜拉卡罕(Abdulkahan)是新疆东部的一位哈密热瓦普制琴师,我听他们说,如果制琴师可以从朋友那里得到倒下的树干或者树木,他们会非常开心可以拥有这些木材。有些制琴师为了能够达到当地人的审美要求,会非法砍伐树木和进口动物皮。当今,很多住在经济落后和生态薄弱地区的制琴师愿意接受来自林场种植的木材,这些是为支撑全球林业而种下的树木。由于快速生长的原因,这些木材并不能提供最佳的密实性、灵活性或者音乐的共鸣等。制琴师知道可以通过调适来改善木材的效果。然而,目前值得担忧的是,由于原材料的迅速减少,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乐器变迁的步伐也加快了,这会突破“当地人可接受的声音”这个审美基准。我也见过不少失败的适应性行为,如使用的木材年龄过短、廉价的合成胶水等,导致乐器容易变坏或跑弦。
制琴师不仅对一定群体的音乐价值观有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对某个地区及其资源非常熟悉。长颈鲁特制琴师使得全球的木材、动物皮和骨得到流动,关注声音以及由于环境、经济和生态变化所带来的对可获取资源的不断变化。商贸之路为过去的制琴师提供了很多机会,给他们带来了木材、动物皮还有其他材料,如装饰乐器的贝壳。那些成为制作长颈鲁特的标准材料,特别那些一直在欧亚商贸之路非流动地区得到使用、以及由于可用性而被采纳的材料,也成为了身份的美学标记。在社会和文化背景下,赋予树木果实以及动物的肉和奶的价值,使得他们的作用已超过了材料的声音共鸣特征。由于乐器随着商贸之路得到不断的设计和修改,在更早期的年代里已逐渐建立起特定的音质和共鸣特性。
在更早的时期,商贸之路沿途发生了怎样的适应和创新?材料由于贸易得到流通,环境由于气候和人类对土地的开发利用发生变化,新的机会会出现在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汇点。结合历史数据,包括那些关联人类活动以及世世代代得到偏爱的乐器制作材料的生物文化信息,应对环境和生态经济的鲁特制琴师们所采取的适应性行为表明,我们看到相似的设计是很有可能的。商贸之路展现了长颈鲁特制作的延续性,不仅体现在那些分享音乐想法并且影响乐器结构发展流动的人们(可以从欧亚地区乐器之间的紧密关系中发现这一点),也体现在那些对制琴师可用的材料以及他们对乐器发展过程发挥的重要作用,更体现在了地区音乐特色的特定音质中。

参考文献
Aubaile, Françoise. 2012. “Pathways of Diffusion of Some Plants and Animals between Asia and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 Revue d’ethnoécologie 1. https://ethnoecologie.revues.org/714 (accessed 31 January 2017).
Baily, John. 1976. “Recent Changes in the dutār of Herat.” Asian Music 8(1): 29-64.
Bates, Elliot. 2012. “The Social Lives of Musical Instruments.” Ethnomusicology 56(3): 363–395.
Bocharnikov, Vladimir et al. 2012. “Russia,Ukraine, the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 In Traditional Forest-Related Knowledge Sustaining Communities, Ecosystems and Biocultural Diversity, edited by J.A. Parrotta and R. L. Trosper, 251-279. Berlin and Heidelberg: Springer.
Brémaud, Iris. 2012, “Acoustical Properties of Wood in String Instruments Soundboards and Tuned Idiophones: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31(1), Pt. 2: 807-818.
Bucur, Voichita. 2006. “Wood Species for Musical Instruments.” In Acoustics of Wood, V. Bucur, , 173-216. Berlin and Heidelberg: Springer.
Dawe, Kevin. 2011. “The Cultural Study of Musical Instruments.” In The Cultural Study of Music, edited by Martin Clayton, Trevor Herbert, and John Middleton, 195-205.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Press.
During, Jean. 2012. “The Dotâr Family in Central Asia. Organological and Musicological Survey.” Porte Akademik. Organoloji sayasi: 93-102.
During, Jean, and Jonathan McCollum. 2014. “Tar.” In The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al Instruments, 2nd ed., edited by Laurence Lib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zhangaliev, A.D. 2003. “The Wild Apple Tree of Kazakhstan.” Horticultural Review 29:63-303.
Dzhangaliev, A.D., T. N. Salova, andandP.M. Turekhanova. 2003. “The Wild Fruit and Nut Plants of Kazakhstan.” Horticultural Review 29:305-371.
Eastwood, Antonia, et al. 2009. The Red List of Trees of Central Asia. Cambridge, UK: Fauna & Flora International.
Fideghelli, C., and P. Engel. 2014. “Fruit Cultivars Bred by ISF in Relation to Silk Road Specie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ruit Culture and Its Traditional Knowledge along Silk Road Countries, edited. by D. Avanzato. Acta Horticulturae 1032: 221-225.
Forsline, P.L. et al. 2003. “Collection, Maintenance, Characteriz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Wild Apples of Central Asia.” Horticultural Review 29: 1-61.
Fouilhé, E., A. Houssay, and I. Bremaud. 2012. “Dense and Hard Woods in Musical Instrument Making: Comparison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Perceptual ‘Quality’ Grading.” Acoustics 2012. Proceedings of the Acoustics 2012 Nantes Conference.
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http://www.iucnredlist.org/
Karychev, Raul K. et al. 2005. “Tree Fruit Growing in Kazakhstan.” The World of Horticulture 45(4): 21-23.
Merriam, Alan. 1969. “The Ethnographic Experience of Drum-making among the Bala (Basongye).” Ethnomusicology 13(1): 74-100.
Moran, Emilio F., and Eduardo S. Brondízio. "Introduction to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Research.” In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Current and Future Directions, edited by E. S. Brondízio and E. F. Moran. Berlin and Heidelberg: Springer.
Parrotta, John A., and Ronald L. Trosper, eds. 2012. Traditional Forest-Related Knowledge Sustaining Communities, Ecosystems and Biocultural Diversity. Dordrecht and Heidelberg: Springer.
Pearce, Tristan, and Ashlee Cunsolo Willox. 2015. “Inuit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TEK) Subsistence Hunting and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in the Canadian Arctic?” Arctic 68(2): 233-245.
Pegg, Carole. 2001. Mongolian Music, Dance, and Oral Narrative: Performing Diverse Identiti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icken, Laurence. 1965. “Early Chinese Friction-Chordophones.” Galpin Society Journal 18: 82-89.
———. 1975. Folk Musical Instruments of Turke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ollegioni, Paola et al. 2015. “Ancient Humans Influenced the Current Spatial Genetic Structure of Common Walnut Populations in Asia.” PLoS ONE 10(9).
Pollegioni, Paola et al. 20154. Landscape Genetics of Persian Walnut (Juglans regia L.) across its Asian Range.” Tree Genetics & Genomes 10: 1027–1043
Post, Jennifer C. 2015. “Reviewing, Reconstructing and Reinterpreting Ethnographic Data on Musical Instruments in Archives and Museums. ” In Research, Records and Responsibility: Ten Years of PARADISEC, edited by Amanda Harris, Nick Thieberger, and Linda Barwick, 135-161.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Qureshi, Regula. 2000. “How Does Music Mean? Embodied Meanings and the Politics of Affect in the Indian Sarangi.” American Ethnologist 27(4): 805–838.
Rancier, Megan. 2014. “The Musical Instrument as National Archive: A Case Study of the Kazakh Qyl-qobyz.” Ethnomusicology 58(3): 379-404.
Roda, Allen. 2013. “Resounding Objects: Musical Materialities and the Making of Banarasi Tablas.”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Sakata, Lorraine. 1980. “Afghan Musical Instruments. Dutar and Tanbura.” Afghanistan Journal 5(4): 150-2.
Shaumarov, Makhmud et al. 2012. “Participatory Management of Desert Rangelands to Improve Food Security and Sustain the Natural Resource Base inUzbekistan.” Rangeland Stewardship in Central Asia: Balancing Improved Livelihoods,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Land Protection, edited by Victor Squires. Berlin and Heidelberg: Springer.
Slobin, Mark. 1969. Kirgiz Instrumental Music. New York: Society for Asian Music.
———. 1976. Music in the Culture of Northern Afghanistan.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 1977. Music of Central Asia and of the Volga-Ural peoples.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Asian Studies Research Institute.
Stock, Jonathan. 1993.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Chinese Two-Stringed Fiddle Erhu.” Galpin Society Journal 46: 83-113.
Thrasher, Alan R. 2000. Chinese Musical Instrumen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rasher, Alan R. "China: Musical Instruments." Grove Music Online. Oxford Music Onl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ccessed January 29, 2017).
Turner, B. L. et al. 2007. “The Emergence of Land Change Scienc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ustainability.” PNAS 104/52: 20666-71.
Vahdati, K. 2014. “Traditions andFolksfor Walnut Growing around the Silk Road.”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ruit Culture and Its Traditional KnowledgealongSilk Road Countries, edited by D. Avanzato. Acta Horticulturae 1032: 19-34.
Vavilov, N.I. 1930. “Wild Progenitors of the Fruit Trees of Turkistan and the Caucasus and the Problem of the Origin of Fruit Tree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Horticultural Congress, 271-286.
Wegst, Ulrike G. K. 2006. “Wood for Sound.” American Journal of Botany 93(10): 1439–1448.
Wong, Chuen-Fung. 2012. "Reinventing the Central Asian Rawap in Modern China: Musical
Stereotypes, Minority Modernity, and Uyghur Instrumental Music." Asian Music 43(1): 34-63.
Wood, Frances. 2002. The Silk Road: Two Thousand Years in the Heart of Asia.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Yoshikawa, Shigeru. 2007. “Acou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Woods for String Instruments.”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22(1): 568-73.
Yoshikawa, Shigeru. 2007. “Acou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Woods for String Instruments.”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22(1): 568-73.
Zhang Baiping et al. 2007. “Multifunctional Mountain Forests in Arid Land: The Tienshan Range in Xinjiang of China.” http://www.mtnforum.org
(编辑:尹翔)
本文的中英文双语版收录于
韦慈朋、萧梅主编:《丝绸之路上的抱弹类鲁特: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从古代到当代表演》,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9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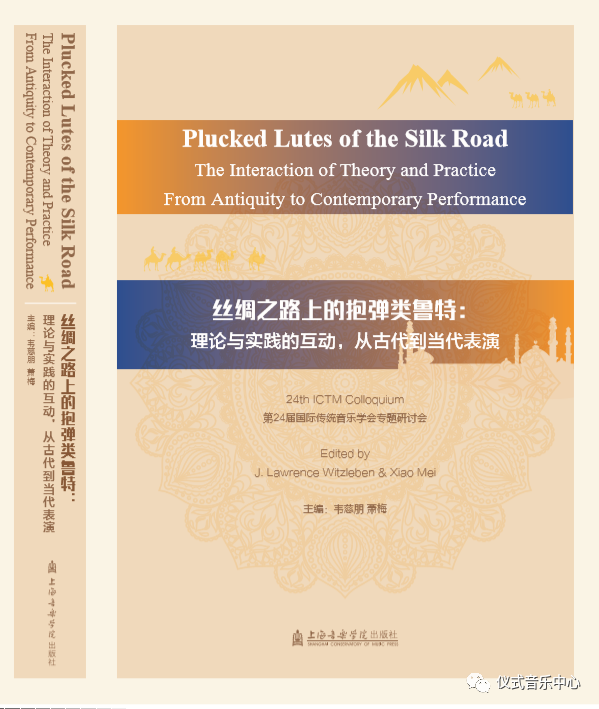
扩展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