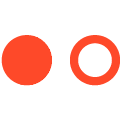(2020年4月)矫英 | 聆听: 声景(soundscape)研究之方法

(Soundscape期刊2000年第1期封面截图)
“聆听”(Listening)是所有现代声音(包括音乐)创作以及声景(soundscape)研究的重要手段。《声景》[Soundscape,是音响生态论坛(World Forum For Acoustic Ecology)于2000年创办的英语杂志。本文是对该刊2000-2011年相关论题的综述研究,也是笔者硕士论文《声音生态学理念下的<声景>期刊研究》的第二章]期刊中聆听与各种研究视角之间的相互对话也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在阅读了《声景》期刊中大量与聆听相关的文章后,决定从该刊中的聆听理念和各学科领域对此产生的具体实践两方面,对【聆听】这一重要的声景研究方法进行概括和分析。
声景期刊的聆听理念
“聆听”是运用人类的听觉感知能力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声”感受的“第一中介”。《声景》期刊的研究不断强化了笔者对聆听的这种感受。从2000年,《声景》期刊第一期即从“聆听”主题开始,至笔者所看到的2011年第十六期的主题“穿过聆听的蹊径”(Crossing Listening Paths),声音生态学研究的这个群体还依然走在聆听的“蹊径”上。可见,声音生态学研究是以“聆听”的方式向多元化研究视角“不断敞开”的。
《声景》期刊有多期的研究主题与“聆听”相关,可以说“聆听”是始终贯穿于该刊16期的各类话题当中,如:日常实践中的聆听让人意识到噪音的存在;盲人的聆听让人们意识到听觉感官的敏锐;聆听教育有可能给医疗、建筑等行业的研究带来帮助;新的电子声学技术带来了新的聆听方式;水下聆听研究;对听力的保护;声音生态学先驱法国实验音乐家皮埃尔·舍费尔(Pierre Schaeffer)的聆听模式研究等。[上述列举的研究角度只是笔者所侧重的聆听的技术研究方法方面,并非对期刊中聆听研究的全面归纳。]
对于聆听研究的认识,在期刊编者社论中进行了较全面整体的分析,把主题与聆听之间的关系有机结合,来强调聆听的重要性。笔者根据期刊各期编者社论对聆听的意义做了总体归纳(1):
聆听的作用
《声景》期刊第四期编者社论中论述:声音生态学是跨学科研究,这个领域研究所依赖的基础形式是通过聆听收集信息,然后进行分析。聆听行为自身,牵涉整个世界,涉及生活的所有方面。聆听是人类最本质的行为。在今天的世界里,聆听可能是一种重要的隐喻:注意到日常生活的即时状况和持续的变化,尽可能的形成对世界环境(world context)的整体觉知。
该刊第一期编者社论中论述:聆听是声音生态学所有工作的基础。没有对进入我们耳朵的声音的认识,没有对输入进来的声音在环境、社会、文化和个人的影响等方面的含义充分理解,就不会有声音生态学的研究。聆听的日常实践发展了我们感知生理、情感和心理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理解的本身是声景研究的重要工具,并为今天的声音生态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动机。另外,聆听创造了环境关系研究领域所需要的连续性。同时,聆听的主题能把期刊中不同领域的研究者所撰写的不同的专业角度和不同行为空间的文章联系在一起。
聆听的重要性
期刊第一期社论:声景研究背景下的聆听始终被视为是深化理解声景研究的重要工作。事实上,聆听被看作是连接声景(Soundscape)研究所有层面的至关重要的工作。从环境、生态学意义和影响的角度来探讨声音研究,聆听的方法是值得信赖的。因此严谨的环境听觉意识与声景全方位的深入研究相互结合和作用是声音生态学研究解决当下世界声音问题的一种方式。
“通过聆听”的目的
期刊第一期社论:期刊的目的不只是呈现知识,更希望激发和吸收人们在此领域进一步研究、活动和思考。期刊也试图“聆听”所有的声音,出版不同地方和文化的文章。当今世界是一个流动的世界,许多人都在迁徙,成为旅者、移民或难民,期刊需要通过以聆听声音环境的方式从不同地方文化的角度来相互熟悉和交流。
美学意义上的聆听
声景期刊第一期,德国哲学家Gernot Böhme在“Acoustic Atmospheres”(2)一文中重拾了被自然科学研究排除在外的,对人的知觉和状态的研究,试图从声景环境空间的角度说明一度被美学史放弃的感官体验与情感表达的意义。从美学角度叙述音乐创作从“时间的艺术”走向“空间的艺术”的变化。其中谈到,聆听从一种体验的工具逐渐成为一种参与世界的形式。作者引用柏拉图的批评——“人们试图通过聆听来发现音程的和谐”,来说明音乐在很早已经作为事件被聆听,而不是聆听“声音本身”。而在声音生态学背景下,“音响事件”就是声音环境本身。Gernot Böhme认为目前从美学意义上对“聆听”描述的最佳模式是:“聆听”是一种对听到的声波震动在思想上的“重演”。(3)
聆听的文化认知
Sabine Breitsameter在“Acoustic Ecology and the New Electroacoustic Space of Digital Networks”(4)一文中,解读聆听的文化认知,认为研究聆听文化声音生态学研究的目的是扩展重要的聆听能力,鼓励声音模式广泛的表达方式和创造性。
聆听的文化认知过程
聆听是“听——理解——学习——融入人的知识或感官系统”的过程。在这个从适应到接受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建立自己的感知能力,把聆听到的讯息转化成个人化的想法、感觉和行为。从这个意义上的聆听是积极的,因为它意味着有意识的参与和努力。
聆听的被动性
聆听的被动特性是由于声音的特性是连续和流动的,也就意味着当你听到声音时,声音的“事实”已经是过去式了,对于声音整体的了解,聆听永远是“滞后”的和“不完整”的。作者认为这似乎与现代社会所强调的主动、高效的选择态度是相反的。
聆听作为训练
聆听是一种训练,聆听者或接收者需要探索和理解声音来关注声音事件的意义。另外聆听者也要对自己耳朵“所听”进行评价和识别。这两点都可以通过实践、锻炼和学习获得。
聆听作为“文化技术”
聆听也一直被视为一种“文化技术” (cultural technique),是指在学校教育中聆听也被视为一种行为标准,这种标准在社会化过程中被教授和被习得,逐渐 “主观化” (internalization),这种文化技术的“控制”特别对事件的复述和语言测试是非常有用的。
聆听与其它形式的关联
聆听与其它适当形式或态度的关联表现在对“标志” (Logos)的感知:对字、词、句、结构、语言、话语类型和表述方式进行确认和解码转译。当然,“声音标志”除了语言声音,也包括音乐和任何其他声音。
声景研究的整体性研究方式也决定了聆听的理论与实践是以整体的研究方式呈现,从一些具体的聆听理论与实践中可以看出聆听方法与不同学科或不同学科的具体问题之间的理论、实践和应用等各方面的紧密结合。很多研究角度都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的结合到了一起,即使是抽象的哲学,如:美国现象学家唐·伊德(Don Ihde)在对聆听的现象学研究中,他通过具体的聆听实践体验去发现和总结出抽象的哲学逻辑。而盲人的聆听是英国宗教学家约翰·赫尔(John M. Hull)根据自己失明后的生活经历,从中提炼出一系列对声音的体验。
因此,声音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生发”的。这就是聆听与各角度研究的关联性方法发展出的声音生态学观念下的独特研究方式。
聆听的现象学研究
众所周知,声音是客观物体振动以声波的形式通过空气或其他物质媒介传播作用于人耳的。所以声音是很难通过形状等视觉认知概念塑造的。聆听的现象学研究把抽象的、听觉意义的声音形式转换成视觉及音乐概念的诠释与规约,扩展了聆听的意义。
期刊在第三期收录了美国当代著名现象学家唐·伊德(Don Ihde)的著作“聆听和发声:声音现象学”(Listening and Voice: A Phenomenology of Sound)(5)的节选:“Shapes, Surfaces,and Interiors”。他试图通过聆听的方式以现象学角度来对形状、表面和内部三方面的视觉描述概念进行剖析,并通过各种具体的聆听体验进行生动说明。
聆听声音的形状和表面
1.“通过盲人聆听”的形状和表面
唐·伊德认为“聆听(声音的)形状和表面”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奇怪的语言表达,这是由于人们可能仍然不知道聆听的所有可能性,但是这可以为盲人敏锐听觉(acute listening)的范式提供一种线索,而在声音聆听方面也给正常视力的人带来微妙的发展可能。盲人使用感觉和听觉对世界的体验通过手杖得以“体现”(embodies)。引用梅洛庞帝的观点:“盲人对行走的体会在手杖的尽头,草地和人行道向手杖透露了它们的表面和纹理。”(6)同时,敲击表面也给盲人带来表面的听觉信息。
2. 通过聆听延展声音的表面
但是唐·伊德认为,盲人和普通人对表面(surface)的聆听只局限于表面,缺乏认识的广度(指对Surface的聆听),这是由于笛卡尔哲学的偏见——来自于“广延性”(extension)观点[笛卡尔的“广延性”指的是物质实体的广延性,也就是通常意义的物体的边长和体积(Surface),在这个概念中并不包含对物体所发出声音的“广延”的含义,笔者理解唐·伊德把物体的Surface被敲击所发出的声音也作为物体Surface作用的一种扩展]。表面与声音有显著的联系:盲人敲击物体所发出的“回声”(echo)是可检测的,由于回声的体验,“听觉空间”被打开;因此Surface回声的距离感觉被呈现出来,回声现象潜藏的声音暂时性也消失了,这属于最本质的听觉空间的意义。对于这种意义的揭示,唐·伊德通过聆听的方法对声音进行测量和“视觉化”的描述。
1)切分法
唐·伊德用自己的体验来说明如何测量声音:
深入揭示听觉距离的方法是用嘴在山或峡谷中呼叫,声波发出再返回人耳的距离可以被体现出来,从本质上揭示了声音空间的所有意义。但是对于这个距离,听觉的判断是匮乏的,相比之下,视觉的判断则更丰富。视觉和听觉对事物的体现会出现时间上的间隔,称为“切分法”(syncopation)。[笔者理解这里的“切分”是指人用视觉、听觉感受到同一事物的时间差间隔,就像音乐中切分音的节奏感带给人的感受。]一个常见的体验是高速飞行的喷气飞机,可以通过声音精准确定它的位置,但当我看的时候已经没有飞机了。声音传播轨迹在视觉表现之后,所以,了解这种“切分法”后,我们听到飞机的声音后,循着声音轨迹让眼睛走在声音之前才能看到飞机。
唐·伊德开始近距离视觉和听觉的“切分”间隔尝试,以便使物体的图像和声音尽可能综合在相同地方。
我站在公园里,谨慎地聆听摩托和卡车开过的声音。即使在地面上声音的反馈还是有一点滞后的。尝试闭上眼睛,跟随着声音马上睁开眼睛,声音反馈的滞后更少了。这再次证明了视觉与听觉的反馈间隔与声音传播的时间性有关。
2)聆听回声的形状和表面
唐·伊德认为“回声定位”(echolocation)是一种不容易练习和被忽略的,其空间意义可能需要强调。回声(echo)的形状(shape)和表面(surface)是模糊的。古老的视觉理论设想从声音到反射物体再回来的是一个射线的过程,作者认为可以成为声音发出的回声的形状和表面。盲人的聆听和感知更加精确,用手杖点击来制造这种听觉的射线(ray)。但是,由于人对听觉空间感知能力的匮乏,有很多事物的存在就感觉不到。
唐·伊德更专注的聆听回声给他非常模糊的“表面存在”(surface presence),击打物体表面得到的回响更丰满。即使回声很弱,他也努力聆听物体的表面样貌。随着聆听能力的不断敏锐,声音回声的表面样貌也不断变得清晰。
聆听的内部
唐·伊德认为声音的“内部”(interiors)是丰富的。他称之为“hear interiors”——“听见内部”。他认为伴随听见内部的声音,听觉能力所呈现的(或说能感受到的)是一种无形,这也是视觉论思维无法企及的方面。去想象普通环境,特别是弱声和不透明的物体内部,事物是由不明显的、隐藏在内部的东西体现。想要看到这样的事物的内部可能需要使用暴力打开它。而这样的事物可以通过其内部的声音来展现。
这样的分析依然是通过具体的实例进行说明得到,唐·伊德谈到:
几个被刷了油漆的球,它们光亮的外表隐瞒了它们内部的属性。敲击其中一个就会发现声音迟钝的没有回声的,可以判断是由类似铅的重而软的金属做成;而另一个被敲击发出的声音可以听出来是木制的;第三个发出的像铃声,由此判断它使用铁或铜做的。每个例子比表面的呈现更能体现听觉的本质。甜瓜的成熟度、冰的厚度、半杯水的容量以及水的容器等,虽然是封闭的,但都可以通过内部的声音准确显示其容量。“聆听内部”(hearing interiors)是声音本质意义的部分体现,是人希望洞察事物内部时通常会采用的方式。只是通常人们不会特别注意到“听见内部”的意义。
这样从形状到表层再到内部的(聆听)活动,具有连续统一体的含义,判断听觉空间意义在这方面的显露是最薄弱的。
唐·伊德认为聆听是一种学习,就像一个从没看见过的盲人,假设当他有能力看见时,眼前的事物也要了解。还有很多丰富的声音存在需要被揭示,对于听觉的空间意义探索是无止境的。通过聆听,我们能听到声音侵入到事物的深层,能听见赫拉克利特的智慧“The hidden harmony is better than the obvious”。
皮埃尔·舍费尔的聆听模式
Frank Dufour在“Musique Concrète” as one of the Preliminary Steps to Acoustic Ecology”一文(7)中介绍了皮埃尔·舍费尔(Pierre Schaeffer)的“具象音乐”理念,作者认为,皮埃尔·舍费尔在对音乐的感知上受到了现象学的影响,他创造的“具象音乐”(Musique Concrète)概念是实验电子音乐研究中重要的创作理念,他认为聆听活动是具象音乐的实践结果。Frank Dufour 的文章全面介绍了皮埃尔.舍费尔的“具象音乐”理念。他认为,“听到什么?怎样描述和证明人们所感知到的内容?”(8)这两个问题是对声音生态学的实践有帮助的。留声机技术(Phonography)不管有多保真,在传达人的体验的时候都是不可靠的。笔者选取了作者对皮埃尔·舍费尔四种聆听模式的介绍。
皮埃尔·舍费尔提出一种聆听功能分析,试图揭示四种聆听模式,每种模式都有不同的声音维度和特点:écouter (Hearing), ouïr (Perceiving or Listening 1), Entendre (Listening 2), Comprendre (Understanding)(详见下图)
皮埃尔·舍费尔的四种聆听模式组合:

- Hearing 声音的捕捉作为索引并指向外部原因。
- Listening 1 指声音本身和把声音作为一种现象捕获,这个声音现象可以设定为各种意义,保有各种效果。
- Listening 2 指声音的品质:持续时间、强度、音高、音色和 纹理(grain)等
- Understanding 指声音作为一种符号放置于既定的意义系统:音乐、语言、社会。
Frank Dufour的分析是,这四种聆听模式既相互排斥,也不总是按相同的顺序被执行。它们在“聆听周期”(listening cycles)、实践、惯习的范围内根据一般感知关系(包括环境、来源、听者、感知范围)被执行。好的声景的标准包括有意义、促进积极聆听和(有)声音的乐趣,可以以此制定系列环境特征,使四种聆听活动形成平衡的循环。
盲人的聆听
盲人的聆听是《声景》期刊的一个重要专题,该刊第三期即由此同名专题。笔者认为期刊之所以会关注盲人的聆听体验,主要是由于缺失视力的人拥有高于常人的听力所带来的特殊感受,听觉的敏锐对盲人来讲是其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具有视觉能力的人可以用视觉完成的部分日常活动体验,但对于盲人,这些体验却完全需要用听觉或其他感官协助完成,这种特别的“实践体验”是考察人的听觉与其它感官之间相互关系的好例证。
“回归聆听”的意义
1.“听觉主导”
过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更多的体会到听觉的作用,如用钟声召唤学生上课,用声音告知人们一天的结束,夜间的犬吠声等,日常生活中不同声音都有其特别的意义。如今的声音环境的辨识度更高,在城市居民甚至乡村居民的周围,陆地、空中都充斥着马达、机器的声音以及家庭环境中的家用电器等,声音环境中的音响代码为发生的事件提供了明确的信息,这比视觉文本更直接。
2.“听觉主导”被“视觉主导”取代
人的生理机能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视觉取代听觉成为信息收集的主要感官。印刷术的出现结束了听觉的统治地位,人们更多的通过文本和说明再现世界,日常生活中充斥大量视觉媒介,如电视、杂志、报纸、网络等,这已经成为一种验证世界“真实性”的方式。而听觉的作用变为引导视觉的作用。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是通过视觉空间来界定和建立世界的。
3.回归聆听
没有视觉能力的人,他的空间感官知觉是被听觉和触觉来定义的。盲人的聆听让我们返回到自己的耳朵,我们应该成为“声音现场”(auditory scene)的忠实的聆听者和解释者。声音看起来是存在于客体之外的,也不知道从哪里发出。建筑空间由人的体验被界定为“流动的音响”(acoustic dynamics)。从辨别声音的运动和空间角度看,穿过繁忙的街道也成为一个复杂的过程。从视觉方面,音响空间是没有边界的。音响空间是球型的、无方向的,声音发出的瞬间就已整个环绕聆听者,没有过去和未来。“听见声音”更重要的是其强度的结果,而非声音来源的固定位置。
联合式聆听
该刊第一期Darren Copeland发表了“联合式聆听”(Associative Listening)(9)的论文。他自2000年起一直参与声音生态学论坛和联合组织加拿大声音生态学协会活动,多次担任加拿大声音生态学协会主席、秘书、记者等职务,1996—97年Darren Copeland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进行硕士学位的研究课题(10)——制作声景纪录片,调查在“视觉中心”的社会中盲人的聆听和功能。Darren Copeland在伯明翰期间对伯明翰大学宗教教育学教授John M. Hull(11)进行了专访,该论文由此产生。作者从四方面问题与John M. Hull展开了有关“联合式聆听”的对话:
1.声音的边界
对于失明同时耳聋的人来说,皮肤是其体验的测量和判断(perimeter)工具,用触觉感知身体、香气和微风。如果外界事物不是以某种方式接触皮肤,对于他来说就是不存在的。所以John M. Hull凭借自己的声音体验认为雷声像“刮”和“抓”(scratching)的感觉。他是用皮肤的感觉感受雷声。John M. Hull告诉有视觉的人如何感受声音:首先必须依靠想象,想象自己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中,外在环境对于你来说是完全不存在的,声音会告诉你位置。他认为声音环境对盲人来说是外在世界的“呈现”。
2.声音空间的即时性
John M. Hull说明像视觉上由远及近的中介空间对于盲人来说是没有的,事物或者存在,或者不在。
3.“移动即存在” (To move is to exist)
盲人感受的空间处于永恒运动和变化中。声音是动态的和短暂的。声音变化是无法预料的。John M. Hull体验到盲人的世界永远是动态的,有视力的人的世界是动态和静态两种。对盲人来说,没有“运动”,世界就消失了,因此,“移动即存在”。
4.噪音的入侵
由于盲人是通过声音感受世界,因此,似乎不需要噪音。但John M. Hull指出普通人可以闭上眼睛拒绝接受不喜欢的事物,但是盲人却无法“关闭”耳朵拒绝不喜欢的声音。
Darren Copeland针对联合式聆听问题与John M. Hull的对话显示了盲人“沉浸”(immerse)于周围环境的主要渠道是通过耳朵的聆听,体现了听觉体验的重要性。John M. Hull对环境声音的敏感度告诉我们声音如何占据和建构了更深的情感体验,声音环境也是体验的载体。但是由于有视觉能力的人往往缺乏对声音的敏感度,因此,人们缺乏用声音表达其承载的社会意义的能力。声音的功效被低估,但事实上声音的关联属性有助于理解声音与其他体验之间的关系,例如情感。Darren Copeland认为,盲人所有感受的基础来自“聆听”。
盲人听觉与触觉的交互
John M. Hull的“Sound: An Enrichment or State”(12)是他于2001年参加英国声景协会(UKISC)会议中的讲座记录。John M. Hull曾经拥有视觉能力,由于患白内障,他的视力在20年间不断恶化,直到最后失明。John M. Hull的自传体著作“Touching the Rock”经常被声景研究引用。在书中,他经常会与有视力的人相比较,从不同的感觉形式比较日常生活体验,认为人可以通过聆听塑造世界和自己,被声音“联合触发”。John M. Hull认为盲人生活在听觉世界当中——“I don’t study sound, I live in sound.”是盲人感知声音的一种状态,盲人的反应是多变的。而具有视觉能力的人是生活在视觉中心状态,这埋没了他们的其他感觉能力。“Sound: An Enrichment or State”这篇文章通过描述日常生活的一些行为习惯来说明听觉体验与触觉体验共同维持聆听感受:
1.盲人&声音VS. 常人&光亮
作者通过举例说明:能见者进入黑暗的房间首先是找开关,但是盲人认为墙上是否有开关没有分别。光亮和黑暗对盲人来说毫不相干。由此看出,光亮和黑暗这个看似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在盲人的感知中是不存在的。白天和晚上对他来说都一样,想要察觉一天的变化是体会自己的胃部是否饥饿。
作者描述其进到房间所做的事情:1.拿出便携式收音机;2.会接近某物体——床、橱柜、放下背包;3.打开收音机。所以,盲人对待声音就像能见者对待光亮。因为作者认为,能见者所感受的声音中一定充满非常丰富的视觉图像,而并不是用听觉来取代视觉。许多音乐家试图使声音与光亮等价。用声音表现光线,但也只是类比。
2.盲人的空间体验
作者说雷声对他来说像“scratching”,因为盲人生活在“无限”的空间,除了他脚底下踩着的地方,也没有屋顶的体验。所以雷声对于他来说没有空间的障碍,而皮肤是自己身体与外界的边界,通常体会不到皮肤的存在,但是突然发痒时能体会到,于是你会碰触到皮肤,发现它有一层膜。除此之外,就不会再有空间的概念了,人的身体就是意识的直接体现(an embodied mind)。皮肤把人与世界相区隔。这里讲的是“皮肤的意识”(属于embodiment),对于作者来说,雷声就像是“屋顶”,能防止他在可怕和失去方向感的无限空间中迷失。
3.回归原始感知能力
在作者失明之后,他试图忘掉光亮的记忆,试图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The place where I am”。(13) 因为当他在失明之初时,所有视觉画面消失,会让他感觉他在所有的事物之外,他的意识脱离身体存在于空间中。所以在他视野中消失的树,作者尝试用手臂抱住树给他带来了美妙的体验,这种体验是长期的,冬天树被风吹发出的口哨声,春天的树发出嫩芽,是松软的,夏天像大海——声音像海浪翻滚,秋天的树声音稀稀拉拉的,秋天的树很有用,树叶掉在路上,根据叶子来判断所走的路,是水沟还是人行道。用叶子判断季节。然后作者发现聆听树叶的空间是无限的,可以不断获得很多细节。
John M. Hull认为盲人感知的特殊性来自大脑的整理,并不是什么神奇的、只有盲人能做到的感知。盲人的感觉是真实的,也许来自盲人身体的(bodily)原始意识——运动感觉(kinaesthesia),而视觉也许是有视觉能力的人潜意识中另外一种原始的身体认识。而看得见的人通过训练也是可以获得盲人身体的原始意识(即运动感觉)。
4.通过“联合触发”的聆听练习
作者描述自己的感觉:我在下雨时对各种物质客体的感觉都是依靠听觉获得,雨声联想到情绪,然后是下雨时树叶的声音,作者假设其为一种沮丧的情绪,随后这感觉不断加深加长直到深不可测的状态。当忘记迷失感后,他开始专注声音的聆听,能感觉到时间,感觉到暴风雨,感受到风,雷声充满房间每个角落,哨声掠过屋檐。作者把鼻子压在窗玻璃上,直到玻璃仿佛消失了,逐渐地鼻子失去意识(应该指感知的意识),我开始逐渐感觉到(aware)雨水打在玻璃的不同部位声音不一样,接着感觉倒雨水打在墙上,雨水打在草坪上和打在小路上不一样,打在汽车上的“嗖嗖声”。作者在努力训练精确细致的聆听,描述一系列雨点与各种物体碰撞发出的声音,用词语来描述声音如:雨点打在窗上有一点“回声”,雨点打在墙上听起来有点迟钝的感觉。
John M. Hull强调“专注聆听”(Listen intently),这使他能从周围环境的声音细节变化中区别不同的声音。这是一种对声音瞬间的感受。作者最后觉得他已经不是在聆听了,“因为雨声不是掉到耳朵里而是掉到他的心里”(14)。
5.感官间的对话
首先作者认为感官之间是有相互呼应的:大多数人认为,人的五官各司其职,但这只是部分事实,当你专注聆听时(Listen intently)你会忽视耳朵的存在。就像眼睛在看的时候,其实大多数有视觉能力的人未必意识到是在用眼睛看,因为人不能看见自己的眼睛,所以确切的说,眼睛是意识到“看见”的。也就是说,眼睛的“看见”是由其他感官感受到的。同理耳朵所听到的声音也是可以通过其他感官“感受”到。你不是用耳朵听,而是用整个身体听。作者是把耳朵和眼睛以同等的方式来思考,这样的办法使他学习用听觉来代替视觉。无论视觉还是听觉最后都被归结为用整个身体来感知(perception)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整个成为一个原始的生物体,成为一种返祖现象的生物。因为他学习用整个身体去“看见”。盲人使用其皮肤去“看见”,应该说他们有机地进行“感知”(perceive)。
John M. Hull提出了触觉与视觉不可等量(incommensurable)的说法,他试图说:借由他人的文字描述或触摸等并不能真正代替自己用视觉对画面的感受,他的假设是想创造感觉之间的对话。
作者逐渐学会根据声音判断人、年龄、经历等,“发声”是声音的指纹(15),这里就像人回忆某人时会浮现其脸部的形象一样,人也同样会根据声音记忆他人的各类信息,仿佛人的历史被声音编码。
作者认为:对于盲人来说是否声音本身就是一个世界?“通常人们认为我们使用大脑认识世界,但其实我们是在用身体,我们的认知来自身体。但是很少人会意识到看得到的人,是用视觉感官认识世界。而盲人被排除在视觉世界之外,话语是盲人认识世界的手段 。作者认为应该把盲人的世界看作是整体世界的一员,感官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人格的重组,心理创伤的修复,新的运动感觉——视觉、嗅觉,触觉的重新组合。声音的象征意义是:“它像桥梁链接听觉和视觉两个看似孤立的世界 ”,这种认识扩展了人类的认知。
盲人声音虚拟训练
“盲人声音虚拟训练”(Acoustic Virtual Training for the Blind)一文(16)中,介绍了一套聆听训练课程,专门用来帮助盲人和视觉受损的人,进行聆听训练。三位作者均来自美国俄勒冈州研究所应用计算机虚拟实验室(Oregon Research Institute Applied Computer Simulation Labs,简称ORI ACSL),Dean P. Inman是高级研究员,Ken Loge是项目经理和虚拟设计师,Aaron Cram是软件工程师。整个“盲人声音虚拟训练”项目得到美国教育部赞助。以下是“盲人声音虚拟训练”的主要内容:
1.定位移动训练(Orientation & Mobility Training),简称“OM training”(17)
盲人和视觉受损的人需要依靠听觉感官来弥补视觉的缺陷。学习用耳朵去“看见”是非常困难的,需要相当的时间和经验。这个定位移动训练已被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校使用。有整套的课程和训练专家进行定位移动技巧训练。掌握定位训练技巧的关键是能识别和定位他们身处的即时环境的“声音事件”。
2.虚拟音响模拟(Virtual Acoustic Simulations)
使用一种计算机3D声音模拟系统,这是一项新兴技术。这套多样化且有效率的模拟训练是目前最先进的技术。而这种音响模拟的价值已经在教育和训练中得到了认可。众所周知,运动系统的训练是复杂的,而这套系统能用电脑模拟真实环境,确保有效性和安全性。这种犹如身临其境的训练可以重复练习,还能动态地增强具体的听觉刺激,有选择地减少“噪音”,指导学习者逐渐认识到需要“听什么”。
3. 声音定位和合成声音
通常,人们用耳朵来进行音响信息定位,被称为“双声道”(binaural)聆听。声音定位指的是人能确定其周围声音发源位置的能力。空间聆听指的是感知位置、大小和声源的环境背景(18)。虚拟三维空间声音环境,是一种被证实近20年的3D虚拟空间声学技术。被普遍用于航天科技领域。被称为“NASA”系统,目前俄勒冈州研究所应用计算机虚拟实验室能采用这门技术来进行虚拟训练研究。用计算机声音处理卡模仿真实的双声道听觉体验,数码技术操控声源。3D声音处理应用现在可以在个人电脑上操作。
听觉与触觉的交互理论
文章“Recovering Narcissus: Sound and Touch in the Digital World”(19)是Tim Wilson对感知变化领域的重要理论家——Derrick de Kerckhove [1983——2008年任多伦多大学法语系教授,多伦多大学信息学院麦克卢汉文化与科技中心主任。中心专门研究麦克卢汉及其他传播学家] 的电话访谈,文章主要讨论声音和触觉与数字科技的关系。重点强调新的交互技术(“new interactive technologies”)和它们在听觉感知上的文化影响。这个问题汇集了很多艺术家、理论家及宣传家的思考。
(一)Derrick de Kerckhove认为网络和多媒体工作给我们一种“环境感知”,针对Tim Wilson的提问——这种观点是否更多的指精神和文化层面的意义?Derrick de Kerckhove认为这种感知将推动对环境的认识,更多的交互性产生更多的触觉。他的整体观点是指出人类从“听觉表达”社会走到“文字表达”社会的转变过程中,遗失了“身体”(感知)部分。人类对“身体”(感知)的抑制,并开始被我们的思考和想象综合重组成一个抽象的方式。把人身体的相互关系脱离肢解。然后虚构了戏剧、理论、虚构了一切,排除直接的联系、直接接触人或事,而失去了真正的交互作用(人自身器官之间的交互)。但是交互系统找到了新的重点:就是人与其关注的客体之间在身体上的交互,这成为“触觉感知”。而听觉往往与触觉相结合,这种结合(audio-tactile)被Derrick de Kerckhove称为“第二触觉”。就像“第二听觉”专指数字媒体制造的脱离自然声源的声音,是加工的声音。这种说法与Murry Schafer称为“schizophonia”(分裂音)相类似。Derrick de Kerckhove对这种“第二触觉”或“第二听觉”的态度是中立的。在文字社会中,人们失去了所有感知能力(指身体的),让书写文字成为抽象文本。
(二)Tim Wilson提出关于聆听方式问题,现在人们的聆听体验多是用随身听边走边听,可以改变音量,形成夸张的音乐或声音。Derrick de Kerckhove认为,聆听属于自己的声音轨迹,使声音符合行为,成为人的行为的伴奏,这种方式是成立的。因为人的“意识流”随时都会出现,如果把它与音乐相互融合,人们就会随着这个“情感结构”的线索做出一些行为。虽然这会错过真实声音环境的接触,但同时我们可以通过编辑自身及情感来适应自己感兴趣的某类模式。
(三)Tim Wilson提出关于声音视觉化导致“听力的混乱”,人们不再仔细聆听,这种情况Derrick de Kerckhove认为也是由于“文字系统”,最直接的行为是通过对声音的解释代替声音本身,如乐谱。
声景教育中的聆听实践
声景教育是由默里·谢弗尔提出的声景教育理论:
声景教育与聆听的整体认识
Vincent Valentine的“Soundscape Education as an Essential Part of Integral Music Education”一文(20)中认为声景教育是音乐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WFAE的声景教育活动从1990年开始,虽然所有的音乐都是世界声音的一部分,但是,默里·谢弗尔意在进一步使人类成为能够联合聆听、分析、再创作声音环境的听众、诠释者和创作者。
Barry Truax在文章“Acoustic Communication Studies at Simon Fraser University”(21)介绍早期默里·谢弗尔声景教育情况时谈到:当时在西蒙弗雷泽大学传播学领域的研究,主要还是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声音研究在传播学领域被低估,把声音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基础之一是新颖的话题。默里·谢弗尔的专业背景是音乐和教育,他的兴趣是在艺术和人文学科领域广泛的结合,他具批判性的社会观点及自觉的环保行动的责任感等形成了其卓越的研究背景,并始终保持声音生态学问题所强调的跨学科的研究观点。
声景教育的聆听实践
1.聆听评论分析(listening commentary analysis)
Barry Truax在“Acoustic Communication Studies at Simon Fraser University”介绍1974年开设的“音响通讯”(Acoustic Communication)的课程中设定了8个主题研究问题,之后又加入了聆听评论分析(listening commentary analysis)。早期课程提供的有价值的惯例始于“聆听”和“听觉感知”(aural awareness,来自默里·谢弗尔的“earcleaning”的概念,可见其著作“Ear Cleaning”的专门论述)。音响通讯的课程从“耳塞评论”(earplug commentary)开始,从“耳塞”开始听觉意识的训练,看似有些矛盾,其实是为了挑战学生的习惯,人为地改变他们听觉的灵敏度。如,一些被忽视的声音突然消失然后再出现,这是一种强迫和压制性的训练。但是通过这种训练方式,可以感觉到(听觉灵敏度)提高,令人随时警觉“声音消失”的问题。当拿掉耳塞,人就很容易注意到生动的听觉变化,这就是人们强化听觉意识的体验,因为在正式聆听环境声音之前,人已经重新调整到了更低的听觉极限,这要比真实环境的声音等级更低。
Barry Truax发现,学生们通过训练意识到,不管他们以前对声音或音乐的兴趣程度多高,这个课程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交的重要方面打开了他们的耳朵和思维,也能够感受到默里·谢弗尔所“预见”的“生命存在的危机”。1974年的这组学生通过课程训练及细致的思考得出了具代表性的结论:初秋,我们把提前预设的问题带到研讨会上,我们大多数都是被视觉认知模式建构的,通过三个月的课程,我能够消除视觉障碍并重新评估周围环境中声音的意义。我的耳朵开始对技术(设备发出的)声音非常敏感,这些声音属于大多数公众认可的或是容易被忽略的声音。我也从秃头鹰濒临灭绝的事情上认识到了自然声音环境的价值。
两个教育活动:
“Sound Presentations”是在默里·谢弗尔的创意音乐教育活动基础上,学生们进行声音或音乐的创作表演,并伴随着个性化的聆听。
讲座,两个小时,以便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小组聆听。其中有两个“寂静”(Silence)主题的表演,第一个小时的讲座,保持完全不说话、在投影仪上打上关于“寂静”的引文,但是听讲座的学生可以用随意的音量读出引文。慢慢的,学生逐步建立起朗读引文的速度。第二个小时,作者表演了约翰·凯奇的“Lecture on Nothing”,这个表演来自凯奇的著作《Silence》,根据其文字记录,凯奇认为文本中嵌入很多“Silence”,要思考在这个实践中文字是如何“组织”“Silence”的?如何认可被体验到的“Silence”?
2. 集体聆听课程
Michael Cumberland的“Bringing Soundscapes Into the Everyday Classroom”一文(22),根据默里·谢弗尔的声景教育理论在教学活动开展集体聆听课程。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人无论如何仔细,随着时间边听边写,都不可能聆听到声景的全部细节,因此,许多耳朵一起聆听可以更全面的听到更多细节。
聆听实践步骤:
第一个聆听清单:选择自己喜欢的声音环境。然后课堂讨论如何设定自己聆听的位置?听到了什么?(包括喜欢的和不喜欢的声音),发现多数选择安静的环境。从中发现不好的声音总是盖住好的声音。第二个聆听清单:老师选择一个学校附近的安静的自然保护区,运用默里·谢弗尔在著作“A Sound Education”中规定的练习列表(23)的第三个列表:是在“Soundwalk”中聆听,这是一种行走在自然保护区或穿过繁忙的街道的不同聆听技巧。
用聆听清单创作声景图表:学生在老师指导下选择和发明符号,用符号表达声音,垂直线表示乐器,水平线表示时间;这一部分作者使用默里·谢弗尔的《The Tuning of The World》一书中6、7章的相关理论来指导学生如何把声音转化成表达符号。
完成图表后,学生被要求把声景图表用人声唱出来,努力把写下来的符号用声音精确地表达出来。如模仿蟋蟀唧唧声等,发掘各种发声的潜在能力。经过几次预演,练习完成的更好。
然后作者用第二个版本——奥尔夫教学法(主要是木琴等打击乐器),作者认为如果把默里·谢弗尔和奥尔夫两种音乐表演进行“声景录音”,并进行比较,讨论音乐的性质,音乐的意图,从声景中创造的音乐合法性,表演是否精确,通过转译的音乐是否还可以听到音乐形象的痕迹诸如:商业大厦、户外等。
选用声景材料(从聆听中得到的)进行创作,发展成音乐作品,形成二部曲、三部曲、回旋曲、变奏曲等曲式结构。最后,整个作品的声音元素都是声音环境中各种声音,直接用人发出的声音、动物叫声、各种机器的声音等构成。每个作品的录音都存入图书馆,并选择优秀作品开音乐会。表演的意图有两个:第一,学生可以向公众展示自己的知识和技巧,通过创作声景作品而形成对声音环境的深度聆听。第二,强化声景和声音生态学意识。
通过聆听所引起的一些争论:比如有多少种不太明显的声音还需要我们去注意?比如从起初忽略的电脑嗡嗡声到发现这个声音的固定音高(降B),或通过聆听到的人声思考人是否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或独立于自然之外?
声景教育结果:
Michael Cumberland认为整个声景教育实现了两个结果:1)深化其个人的声景聆听体验(遵循默里·谢弗尔教育体系);当把聆听作为一种重要行为,可能产生新的不同——社会状态的变化。2)其根本变化就促使“强化聆听”在学校中流行,将“被动聆听”变为“主动聆听”。
水下聆听
该刊第六期以水下聆听为专题,揭示鲜为人知的水下声音空间以及人所制造的噪音对动物健康和交流造成的影响,从海洋生物研究方面探讨噪音的危害和环境保护问题。期刊编者专门请来了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专家,通过对水下声音环境、聆听、录音的研究和探测来讨论人类社会与海洋生物之间的关系及研究意义等。
“座头鲸的歌”片段
视频来源:https://youtu.be/sjkxUA041nM
20世纪60年代著名的生物学家Roger Payne 和 Scott McVay第一次用水中听音器(hydrophone)探测到海洋声音环境,1970年他们创作了“座头鲸的歌”(Songs of the Humpback Whale),成为最畅销的历史录音,也给海洋生物环境研究带来强大的刺激。30年之后Roger Payne指出了海洋出现的噪音污染问题,“低频”(Low pitch)的座头鲸声音与“高频”(High pitch)的噪音是一种对比,同时也让人在研究水下生物知识的同时了解到更多人类社会的噪音类型。
水下声音探测装置
Michael Stocker在“Ocean Bio-Acoustics and Noise Pollution”一文(24)中论述了海洋水下声景存在的声音类型及如何研究和探测。
作者在分析人为噪音来源时介绍了水下声音探测的装置。1954 年至1955年,美国海军开发了第一个海底监听系统,被称为是“Sound Surveillance System”(“声音监测系统”, 缩写:“SOSUS”)。该系统能够精确监测海洋交通,有能力长距离监控个人船只,确定他们的位置、航向、等级和大小。“冷战”结束后,SOSUS被用于科学研究,观察生物的多样性声音,也发现由人类活动产生的噪音。随着“SOSUS”系统的使用,可以对海上交通产生的噪音进行监督和控制,缓解噪音。
水下聆听体验
音乐家和作曲家Lisa Walker的“Listening Underwater”一文讲述了作者在参与阿拉斯加东南部座头鲸水下声音生态的研究小组时,负责研究鲸鱼的发声,分析了鲸鱼的节奏、曲调类型和轮廓,并阐述了她的耳朵洞察对其科学研究的影响。
由于作者是受过训练的音乐家,对于水下的音响活动的微妙模式感知更敏锐。她用古典音乐的语汇来描述座头鲸的声音,如变奏曲、小号、八度以及主题等。从最初的科学实验的目的,她又发现座头鲸的声音色彩的变化。通过声音来发现海洋生物的觅食及生存技巧,进而发现生物的社会构成和社会关系的形式。
作者通过对实验过程的分析发现鲸鱼发声通过水、仪器设备到人的耳朵这样一个聆听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作者认为科学方法论能克服人的个人因素形成的部分偏见和局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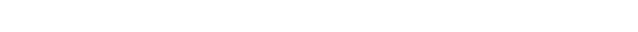
注释:
(1) Hildegard Westerkamp. Spring, 2000. Editorial. Soundscape. Volume 1, Number 1. P3-4.
(2) Gernot Böhme.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Norbert Ruebsaat. Spring, 2000. Acoustic Atmospheres. Soundscape. Volume 1, Number 1. P14.
(3) Gernot Böhme.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Norbert Ruebsaat. Spring, 2000. Acoustic Atmospheres. Soundscape. Volume 1, Number 1. P14-18.
(4) Sabine Breitsameter. Fall/Winter 2003. Acoustic Ecology and the New Electroacoustic Space of Digital Networks.Soundscape. Volume 4, Number 2. P24.
(5) Don Ihde. July. 2001. Shapes, Surfaces, and Interiors. Soundscape. Volume 2. Number 1. P16.这篇文章节选自Don Ihde的著作“ Listening and Voice: A Phenomenology of Sound ” Sound, Ohio University Press, Athens Ohio, 1976 pp. 67-71.
(6) Don Ihde. July.2001. Shapes, Surfaces, and Interiors. Soundscape. Volume 2. Number 1.P16原文:he feels thewalkat the end of his cane. The grass and the sidewalk reveal their surfaces and textures to him at the end of the cane.
(7) Frank Dufour Fall/ Winter 2008. “Musique Concrète” as one of the Preliminary Steps to Acoustic Ecology”. Soundscape. Volume 8, Number 1. P19.
(8) 同上。
(9) Darren Copeland.Spring, 2000. Associative Listening. Soundscape. Volume 1, Number 1,P23.
(10) 信息来自Darren Copeland的个人网站[Online] Available:http://www.darrencopeland.net/biography.html(最后登陆时间2013年4月2日)。
(11) John M. Hull自1989年起担任伯明翰大学宗教教育学教授,英国宗教教育期刊创始人,担任主编25年,国家基督教教育委员会主席,组织国际性宗教研讨会.出版关于探讨非视觉研究期刊:On Sight and Insight: a Journey into the World of Blindness(One World Books, Oxford reprinted 2001)和In The Beginning There wasDarkness published by SCM Press 2001.John Hull的自传体著作“Touching the Rock”经常被声景研究引用。
(12) John Hull. July, 2001. Sound: An Enrichment or State. Soundscape. Volume 2, Number 1,P10.
(13) 同上。
(14) John Hull. July, 2001. Sound: An Enrichment or State. Soundscape. Volume 2, Number 1,P10.
(15) John Hull . July, 2001. Sound: An Enrichment or State. Soundscape.Volume 2, Number 1. P 13. 原文:“The voice is a fingerprint of sound”
(16) Dean Inman, Ken Loge, and Aaron Cram. July, 2001. Acoustic Virtual Training for the Blind. Soundscape. Volume 2, Number 1. P20.
(17) 同上。
(18) 同上。
(19) A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Derrick de Kerckhove and Tim Wilson. July, 2002. Recovering Narcissus: Sound and Touch in the Digital World. Soundscape. Volume 3, Number 1. P15.
(20) Vincent Valentine. December 2001. Soundscape Education as an Essential Part of Integral Music Education. Soundscape. Volume 2, Number 2. P9.
(21) Barry Truax. December 2001. Acoustic Communication Studies at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Soundscape. Volume 2, Number 2. P11.
(22) Michael Cumberland. December 2001. Bringing Soundscapes Into the Everyday Classroom. Soundscape. Volume 2, Number 2. P16-19.
(23)Murry Schafer,R. Murray. A Sound Education: 100 Exercises in Listening and Sound-Making. PDF. p.15-16.
(24) Michael Stocker. Winter 2002/Spring 2003. Ocean Bio-Acoustics and Noise Pollution. Soundscape. Volume 3, Number 2/ Volume 4, Number 1. P16-29.
总策划:萧梅
文字:矫英
编辑:尹翔
输12
【声音研究专题】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