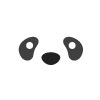【工作坊综述】传统、现代与个性
——邓建栋二胡讲座
时间:2018年12月20日15:30-17:00
特邀名家:邓建栋
课程主持:萧梅教授
综述人:余亚飞

2018年12月20日下午三点半,“民族器乐的传统与当代演释”课程系列工作坊在上海音乐学院中603如期而至。此次工作坊邀请到的是二胡名家邓建栋,主持人是萧梅教授。
在工作坊中,邓建栋开门见山地谈及,曾有人评价他是“融传统与现代、学院与民间为一体的二胡演奏家。”之前一直也未仔细思考过这个评价的具体含义,直到这次受到萧老师的邀请,“传统与现代”这对词语才真正引发了他较长时间的深入思考。
他认为,由于中国记谱法的缺失,可查找的文献记载有限,我们无从考究有曲谱、有代表人物的二胡源流。从有音响、有作品、有曲谱的刘天华和阿炳开始,二胡的历史也不过一百年。如果在漫长人类历史长河中,百年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是这个百年对于二胡的发展来讲至关重要,这时期的发展奠定了二胡在民族器乐中的地位。那么就一百年的时间里,基于阿炳、孙文明和刘天华部分作品创作的语言、手法、曲式、调式(以五声调式为主)、演奏技法、旋律、腔韵等等,我们暂且把它定义为传统作品。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刘天华是中西合璧道路上迈开第一步的音乐家,所以他是横跨传统与现代的第一人,也是传统与现代的分水岭,他是真正意义上使二胡向西方探索、借鉴的先驱。继他之后的刘文金、王建民等作曲家都是刘天华先生中西融合创作之路的继承者,创作思想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作曲家刘文金先生的两部作品《豫北叙事曲》和《三门峡畅想曲》开启了现代二胡创作的新篇章。时隔三十年后的八十年代末,王建民的《第一二胡狂想曲》使得二胡进入了现代作品的演绎。上海音乐学院是中国现代音乐、新音乐的摇篮,特别是起源于萧友梅(上海音乐学院创始人之一,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开基创业的一代宗师、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者)、黄自、谭小麟等人,包括之后的贺绿汀先生、胡登跳先生等。王建民是继他们之后在民族器乐现代化尝试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的四部狂想曲足以使二胡现代音乐创作登上一个新的高峰。邓建栋作为前三部狂想曲的首演者,真正的经历了探索如何诠释这些作品里的新思维、新语汇、新结构、新技法。从他演奏的江南丝竹《行街》到《第三二胡狂想曲》可能有几百年的“时差”,而在两者的文化背景、音乐语汇之间,更让人有“隔世”之感。那么,在二胡演奏中如何切换传统与现代风格的演奏抑或把两种演奏融会贯通,由此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演奏个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缘由和思考,接下来他分别从传统作品演奏、承接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作品演奏、现代创作作品的演奏、个性的形成等四个方面探讨了关于二胡的传统、现代与个性问题。

一、传统作品的演奏
谈起传统作品,他认为,阿炳、孙文明的作品和刘天华的部分作品及其二胡百年历史中一切运用传统语汇、创作技法和演奏手法的作品归结为传统作品(比如《江河水》《一枝花》《秦腔主题随想曲》《兰花花叙事曲》《洪湖》等)。首先,传统作品的特点大都旋律性强,音区不高,演奏上均使用传统把位和指法,韵味与戏曲声腔及民间音乐有明显的依托关系。同时,由于二胡几百年来一直作为伴奏乐器在戏曲中存在,脱离戏曲作为独奏乐器也是从刘天华先生改革之后才开始。所以在二胡传统作品中戏曲和民间音乐的痕迹是非常重的(如《二泉》《月夜》《闲居吟》《良宵》《流波曲》中运用锡剧、道教音乐、江南丝竹、江南民间小调等,《弹乐》《杜十娘》运用苏州评弹的唱腔和弹拨乐器的演奏手法等)。由于传统的音乐氛围浓郁,地域文化的不同,加之交流的相对闭塞,致使个人演奏色彩浓郁、鲜明,差异性大,容易形成独特门派或风格(比如蒋派)。那么,这些风格的确立在大的时代背景下来看,其音韵、音调均体现出中国线性旋律美和传统意境美的特点。
通过邓建栋个人曾经从事戏曲音乐和民间音乐学习工作的经历,他认为浸染在民族民间音乐中的这种学习经历,对音乐创作与演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这种戏曲和民间音乐的学习是融进血液中的。由此可见,要掌握好传统作品的演奏,需要我们深入学习戏曲音乐、说唱音乐和各地方的民间音乐。并现场演奏一段锡剧及沪剧《紫竹调》,他精湛的演奏赢得同学们的阵阵掌声。
邓建栋不仅探讨了有关传统作品演奏手法的问题,现场还以《二泉映月》为例,表达了他对于传统作品的理解与演绎所秉持的态度问题。谈及“二泉”的演奏,他转述了乔建中所提出的两种处理方式和态度。一种是严格遵循阿炳的历史音响,甚至不惜加以逐句逐个音的模拟和“精仿”,以便让自己的演奏更“像”阿炳,为此,他们力求在细节上做到精细准确,仿佛是阿炳“琴音”的隔世再现。这种演奏我们可以称之为“二泉”演奏上的“绝对客观主义”态度;另一种是比较强调“二泉”作者的悲惨遭遇,努力提炼出某种主观的理解,以表现阿炳的人生悲情和对旧时代的控诉。所以演奏时力度起伏、乐意对比都比较大,个人意识强,主观附加内容多,借此以打动听众的耳与心。这种我们可以称之为“二泉”演奏上的“主观主义”演绎态度。

2017年,他被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评为杰出民乐演奏家时,乔建中受委约撰写邓建栋的评论,并听遍了他所有的“二泉”演奏版。其中有交响乐伴奏版、民族管弦乐伴奏版,还有DVD现场版,结果发现演奏时长相差无几,乔建中认为邓建栋的演奏具有异常的稳定性与精准度。他认为他的“二泉”是介于前面两种处理方式的第三种演绎策略,乔建中称作是“相对客观主义”。他认为邓建栋在演奏时异常冷静客观,把自己的身心“放空”,不刻意强迫听众接受所谓的“景”或所谓的“情”,更不一定要让听众从中联想阿炳的所谓“身世”、“悲苦”、“愤恨”等,而把指下和弓弦间的音乐放在第一位,让音乐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直抵听众的耳际心间,最终营造出与听众用心交流的一种特定语境和特殊氛围,也让听众除了领会理解作品的内涵,也能触摸到演奏者本人的音乐精神和艺术个性。他认为这种“相对客观主义”的主要特点是:不给音乐增添更多的“外加物”,客观而又有所控制地处理音乐的每个细节,把审美感受、艺术想象适度地交给作为个体的每一位听众,由演奏家和听众共同来完成艺术作品的呈现。乔建中作为听众解读邓建栋的音乐,也恰是邓建栋要通过音乐传达的精神,他与听众产生如此共鸣,这也是作为演奏家来讲最欣慰的事情了。

邓建栋现场演奏了《二泉映月》的经典片段,旨在表达他对于传统作品的演奏、对于距离我们有历史感的作品演奏的态度。他认为,我们既不要主观的感觉作者在世,又不要刻意的还原当时,我们的演奏始终要把纯粹的音乐表达放置第一,用一种客观的态度去让观众忽略掉演奏者的人,演奏者的演,而关注于音乐本身所传达出的精神与观众心意相通。当然,由于传统作品距离我们具有一定的历史年代,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我们需要站在当今的文化背景中用一种更高级的、更能融于时代被听众所接受的、更容易产生共鸣的诠释角度去演绎传统作品,使传统音乐得以在新的时代光大、传承下去。传统是相对于现代的传统,现代是相对于传统的现代!因为在历史的时间轴里,谁都不是永恒的。现代与传统总是互为表里、互为统一、不可分割的。
二、承接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作品演奏
邓建栋认为,刘天华与刘文金都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勇于向西方借鉴的音乐家。刘天华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把西方的创作技法和理念,运用到中国民族器乐的创作中,洋为中用,取长补短,丰富了中国民族乐器的演奏技法和表现力。从他的《光明行》《苦闷之讴》《烛影摇红》等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到中西结合的创作之路,也就是用我国的优秀民族民间音乐素材,结合一切可用的传统及西方作曲技法来融合、创作。不仅继承了祖国的民族音乐传统,又开创了中西调和与合作的新路。他创作的十大名曲,为后人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和重要的理论依据。
刘天华的作品还处于乐师本身的非职业创作,到了刘文金那里,就转变为专业作曲家介入二胡的创作了。刘文金的创作方向无一不是对刘天华创作精神的一脉继承,只是刘文金在刘天华的这条探索道路上走得更深,走的更远。他大胆借鉴了西方音乐的创作体裁、曲式结构及和声、复调等创作手法,并采用无伴奏、钢琴伴奏和乐队协奏,把二胡的创作一次又一次推上了新的高峰。(如豫北、三门峡、长城、雪山魂塑、如来梦组曲等)与前人相比,他的作品演奏技法和技术难度更大,色彩更丰富,音响更立体,音乐对比更强烈,表现力更强,二胡已经可以演奏史诗般宏大的作品。作品的体裁结构,与伴奏的合作形式,无一不开创了先河。他的创作是对刘天华二胡创作理念向更深更广方向的发展,同时,刘天华与刘文金的音乐创作都是对西方创作技法和理念的引入与借鉴,以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重新赋予了二胡这件乐器新的生命!
邓建栋指出,两位作曲家的作品作为传统与现代的承接与过渡,都体现了对于我国民族音乐和西方音乐的探求与嫁接。对于这类作品的演奏,我们除了要继续学习、吸收民族民间音乐和戏曲音乐的手法外,也由于作品表现内容发生的变化,需要演奏者技术技巧更大的扩展和提升,同时需要更多的多维音响的感知,来体现作曲家立体思维的延展。我们从关注单一自己的演奏走出来,到多种类形式的合作,到相互倾听,到感受音乐中的彼此,这是作曲家创新思维带给演奏家的崭新体验。应对这些变化,我们在变化中摸索,在摸索中总结,在总结中更新,在更新中去创造!

三、现代创作作品的演奏
从典型性和传播性来看,二胡的现代作品当属王建民的四部狂想曲。(当然,也有其他作曲家的作品,由于邓建栋是其中几部狂想曲的首演,加之其典型性,此处仅以狂想曲为例)作品在创作手法、音乐语言和演奏技法上都是全新的,无一不是带有现代作品的典型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带有革命性的。同时在演奏现代作品,特别像《狂想曲》这样无标题的作品,对演奏者的要求非常高,无论在技术上还是音乐表现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作为“第一狂想曲”、“第二狂想曲”、“第三狂想曲”的首演者,作为一位在此之前专以传达二胡“传统琴音”的他,面对“狂想系列”中一系列高难度技艺和新旋法,一方面邓建栋将之视为他二胡艺术生涯中的一次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把它当成扩展自己艺术视野的难得机缘。他感到这是一个全新的音乐天地,一方面他以此前长期积累下戏曲伴奏和民间音乐的扎实功底为根基,另一方面大胆闯入二胡艺术的这一“现代”探索,最终奏出了属于二胡艺术、也属于自己的全新的“琴音”,这种创新的激情给我带来无比的兴奋。对于一位早已习惯演奏“传统琴音”的他来说,对于早已习惯欣赏简单传统美的听众来说,这无疑都是巨大的震动。在十多年间,连连首演几部二胡狂想曲,勇敢接受现代思维和技艺的洗礼。当然这中间也有过阵痛、徘徊,也不乏引发诸多争议,三十年中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当然,这只是一点点杂音、小插曲而已,丝毫不会影响王建民及其创作在二胡发展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也不会影响他继续为推进二胡艺术的发展坚持前行的信心。
由于现代作品与之前的所有作品都不尽相同,邓建栋还谈了他对于现代作品演奏的一点思考和尝试。主要有调式调性的变化、技术技巧的挑战与储备、综合能力的延展、民族民间音乐素材的捕捉等方面。
(一)调式调性的变化
相对于传统作品来说,现代作品中的调式调性显得更为复杂多变,特别是像《狂想曲》中人工音阶的介入和调式调性的复杂变化,打破了我们原来传统把位的划分,常用的传统把位已经无法适应现代作品的需要,要求我们要根据作品中音阶、音程、琶音等的需要,在传统把位和非传统把位中来回穿梭变化,来适应现代作品中那些复杂的变化。
(二)技术技巧的挑战与储备
作为现代作品成功范例的四首狂想曲中,有着多变的节奏和复合节拍、密集的变化音、连续的轮指、快弓技巧、整段的三连音、快速的大琶音、大段的自由节拍等复杂的技术技巧,以及频繁的转调、离调等。这些与传统技法决然不同的技术都挑战了我们的演奏能力,而技术又是现代作品中音乐表现的重要手段。所以,为了避免过去民乐以曲代功的习惯,没有针对性、系统性的技术训练,导致技术技巧达不到现代作品要求的情况,在我们平时的训练科目中,要有意识、有计划、有针对性的进行各种技术技巧的训练(借用小提琴的练习曲和作品技术难点部分),这些练习,实际就是各类技术技巧的储备,在面对现代作品的一次次挑战中才能自如应对。
另外,还有值得一提的是现代作品对于速度的飙升。速度是技术的一种体现方式,我们说炫技通常都指的是速度。现代作品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对于速度的追求,它好似现代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速度是最好丈量演奏能力的标准之一,高质量的演奏无一不是有出色的速度来保障。这些都需要娴熟的技术来完成,所以储备技术技巧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传统的以曲带练很显然将无法满足现代作品的需要。
(三)综合能力的延展
在演奏现代作品的时候,我们除了要有非常扎实的演奏能力和音乐基础课的训练,还要有其它诸如作曲理论方面的丰富知识,宏观把控作品的结构、曲式等,同时还要大量借鉴西方乐器小提琴、大提琴等演奏技法,还有指序、弓法安排等。也包括其它艺术门类的学习,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和处理。所以努力拓展我们的知识面,才能很好完成现代作品的演奏。
(四)民族民间音乐素材的捕捉
很多现代作曲家虽然用西方的一些创作手法和技术手段,但最终用来加工的还是中国的材料,需要我们能敏锐地捕捉到音乐中带有的民族基因出自哪里。比如说《“第一”二胡狂想曲》是以云、贵地区民间音乐为主要特色素材,宫音上方大、小三度并用的苗族飞歌、彝族阿细跳月的音调及其动感的节奏。《“第二”二胡狂想曲》中典型的小二度、小七度、减八度音程,取自于湖南民歌及花鼓戏中有着特征意义的音程关系。《“第三”二胡狂想曲》新疆少数民族的浓浓风情。《“第四”二胡狂想曲》用独特的西北民谣贯穿全曲。我们在接触这些作品的时候一定要去了解揣摩素材的母体音乐来源,抓住地方音乐语言的特点,就像我们学方言一样,是否做到了学什么像什么,语言道地、纯正。比如演奏《“第二”二胡狂想曲》,邓建栋要求学生去听湖南花鼓戏,从中寻找原始素材的相似母体与二狂比对,并了解花鼓戏的演唱韵味和演奏手法,甚至还可以学唱,有条件的还可以去学学大筒(包括其它主弦)的演奏,通过学习之后的演奏感觉完全就不一样了,演奏就有味道了!如《“第二”二胡狂想曲》中的小快板源自湖南花鼓戏中的梁山调。比如《“第四”二胡狂想曲》中使用了《脚夫调》、《船夫曲》的素材,我们都要去听,去学唱,了解母体。
实践证明,准确的定位作品旋律的母体取材至关重要,这涉及我们是否能准确的理解作曲家的音乐语言,树立鲜明、准确的音乐形象。这也是连接现代与传统的桥梁!邓建栋引用余光中先生在《莲的联想》中的一句话:“有深厚‘古典’背景的‘现代’,和受过‘现代’洗礼的‘古典’一样,往往加倍地繁复而具有弹性。”我们应该把现代放置于深厚的传统中去对待。

四、个性的形成
面对“融传统与现代、学院与民间为一体的演奏家”之评论,邓老师认为是时代赋予了演奏家施展的空间,也是作曲家给予了演奏家发挥的可能。“在传统与时代的上下文中,谁都脱离不了自己身处的背景与基因链。”
大的背景下赋予演奏家共性的特征外,他们的个性差异也因成长背景、个人审美取向、艺术标准而不同,带有强烈的个人特点。邓建栋的艺术道路是独特的,也是不可复制的,他在戏曲学校、戏曲团体的10年学习和工作,以及之后专业的大学教育,塑造了他今天特有的艺术个性。同时,除了艺术经历的背景,个人在艺术创造中所信奉的精神,秉承的原则,也是造成艺术个性差异的因素。
当代德国指挥家瓦尔特说:“演奏家的艺术处理和见解越高,他就能更大程度地传达作品,只有伟大的个性才能明白揭示伟大的创造”。作为演奏家,邓建栋首先对自己树立了极高的艺术标准,成为一个有思想、有较高艺术审美的演奏家,是我不断追求的原动力!演奏家作为二度创作者,其演奏应传达出自己特有的音乐审美观。
邓建栋演奏的标准追求一个“正”字。所谓“正”是指“音正”、“韵正”、“气正”、“态正”、“涵正”!这种演奏标准,他试图体现于我演奏的每个细节之处:“音色纯正”、“音韵适正”、“气息顺正”、“姿态端正”、“内涵诠正”,以求演奏通达自如,神形合一。他力求每首作品演奏的绝对稳定与精细,同时,在稳定与精细的基础上把“情”至于最高地位。他也追求至情至善、饱满深情和感染力,力图努力彰显个性的同时,把“情”放于所有艺术标准之上的最终精神追求。正如柴可夫斯基所说:“只有从艺术家灵魂的深处倾泻出来的音乐,而又被灵魂所感动的音乐,才能感动听众,占有听众。”这也是邓建栋的座右铭!
乔建中先生在听过邓建栋赠送他的CD后曾这样评价他的演奏:“音质纯净剔透,音色甜润清丽,技艺全面成熟,由此形成的个人乐风,则是刚柔相济、收放自如,细腻处如微风拂柳,奔放时有浩然之气。”尽管他认为还没有完全做到乔老师的评价,但这些都将是他永远的追求。

五、互动和结语
在互动的提问环节,邓建栋首先就萧梅教授提出“在传统与当下语境中如何看待二胡的二度创作问题?”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二胡二度创作需要创作者理解作曲家的创作意图,包括谱面上的每一个表情符号、力度符号等。可以说,进行二度创造的前提是首先要尊重作曲家的创作意图。
第二个问题是“与其他演奏者相比,他在多部二胡狂想曲首演过程中,两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他认为在于他更重视和理解创作者的意图以及传统音乐的母体和现代技术的原形。并在现场通过音阶的示范,展示了二胡演奏中对传统技术和现代小提琴等技术的灵活运用。因此,他不主张轻易改变创作者的原有创作意图。
第三个问题是“在作曲家传达的作品本身内涵和演奏家技术表达发生冲突时,演奏者该如何面对?”。邓建栋认为,还是要以创作者本身创作意图为体现宗旨,这本身也是演奏者技术表达时应该处理和调和的关键问题。
综上所述,演奏艺术在邓建栋身上历经了从简到繁的发展过程。从起初简单不换把的戏曲伴奏到演奏中小型的独奏作品,到富有技术挑战的现代作品,他在不断追求技术与艺术中摸索、学习。现代作品开二胡演奏技术之先河是前无古人的,所以像邓建栋这样的二胡演奏家是具有历史使命感的一代!这种尝试如果说成功,可以说,他是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成功范例。传统有助于理解现代,现代有利于展现传统!现代是传统的继承,传统是现代的奠基。所以,传统与现代在二胡演奏中从来就是无可分割、相互依存、一脉相承的!岁月的沉淀给予我对人生的思考、对艺术的深化,他希望它能通达于指尖的每一个音符。

文字:余亚飞
摄影:张珊
编辑:熊曼谕
主办:
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
协办:
香港蓬瀛道教音乐研究基金
项目资助:
国家“双一流”高校建设项目经费资助
上海高水平地方高校建设扶持项目经费资助
(萧梅教授团队“生态音乐学研究”建设项目)
往期回顾:
【工作坊综述】再现之外——谈琵琶专辑《摆》与《蓝·掉》的创作历程
【工作坊综述】“一意孤行”的中国当代音乐隐士:由《山歌》《第二中阮协奏曲》《第三交响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