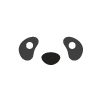从草原到城市
——记“安达组合”上海音乐学院工作坊与音乐会
时间:2018年11月22日15:30-19:00
地点:上海音乐学院学术厅&中603
特邀名家:安达组合
课程主持:萧梅教授
综述人:凌嘉穗
“安达”,在蒙古族语中是“结拜兄弟”、“结盟”之义。2003年,几位志趣相投、才华横溢的蒙古族青年艺术家聚集在一起,求“结盟”之意,取“安达”之名,建立了一支民族音乐团队。团队成员包括那日苏、其其格玛、毕力格巴特尔、乌日根、乌尼、青格乐、赛汗尼亚、阿乌日根、青格乐图,他们是当今蒙古族马头琴、长调、呼麦、冒顿潮尔、蒙古打击乐等艺术领域中青年一代的代表人物。
通过十余年的努力,安达一方面成功打入了海内外的商业市场,是当今屈指可数的实现商业巡演模式的民族音乐团队;同时也得到了专业界、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在高校开启了民族音乐教学、传承、创演、传播的全新探索。此外,安达组合还在海内外多所高校为青年学子举办工作坊和巡演音乐会。

2018年11月22日,安达组合作为“民族器乐的传统与当代演释”课程的特邀团队来到了上海音乐学院,为师生们奉献了一台令人激动又感动至深的音乐会,以及一场轻松而活跃的学术工作坊。

音乐会开始前,学术厅里的听众们就早已比肩继踵。这场由萧梅教授主持的音乐会在一首奔放洒脱的鄂尔多斯《酒歌》中拉开了序幕。台上的马头琴、冒顿潮尔、口弦、托布秀尔,这些都是蒙古族传统乐器,安达把它们从草原带到了都市、带上了舞台,让这些乐器在不同的表演语境中、以别样的方式诉说着蒙古族的故事。


《故乡》这首歌曲改编自蒙古族传统民歌《水灵红格尔米吉德玛》,通过乐队成员乌日根的重新填词和编配,不仅叙说着乡愁,更是注入了一种生态伦理的情怀,表现了对当下草原之殇的忧思与忧伤。其其格玛带来的《苍天母亲》和《我的草原》两首歌曲,是整场音乐会中最为沉静和感动的时刻。马头琴和吉他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伴着那似从天边而来的歌声,观众们彷佛真切地感受到了草原上的凤。


为了与上海听众产生互动,安达组合特意演唱了蒙古族歌王哈扎布演绎过的经典曲目《上海产的半导体》。这首歌是由著名诗人纳·赛音朝格图作词、达斡尔族著名作曲家通福作曲,于上世纪50、60年代创作的,表现了那个时代的大草原与上海所象征的现代社会和先进科技的第一次接触。如同这首《上海产的半导体》一样,安达组合本身也正是传统与当代发生碰撞的产物。


为什么安达能把辽辽草原带到观众们的眼前?为什么马头琴和呼麦成为了蒙古族的文化符号?安达是如何让这些传统乐器和歌唱进入世界音乐市场的?这一系列问题在随后的工作坊中似乎能找到答案。


晚上的工作坊亦是座无虚席,安达组合和大家分享了他们一路走来的经历与故事。萧梅教授在开场主持中介绍到,安达组合有着对传统音乐独特的理解和创新,他们团员之间的默契、情感和对于音乐共同的坚持,是最难得、亦是最令人动容的。安达组合通过其人、其器与其乐,体现了当代语境下民族器乐表演者的多元身份及其主体性,通过他们对于传统乐器创造性的理解、改良与运用,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与表演语境中,探索着传统音乐在当代新的可能。而这些,正是该课程意欲讨论的核心议题。
一、其人·表演者的主体性
工作坊的主讲人是安达组合的队长那日苏,他首先对组合成员做了介绍。“一专多能”是外界对于安达成员共识性的评价。安达成员们不单单是某一乐器的“演奏员”,他们身上集合了创作者、表演者等多重身份。他们表演什么、怎么表演都是作为表演者、同时作为创作者的成员自己决定的。例如那日苏本人,在团队中除了负责马头琴、叶克勒、呼麦的表演之外,还负责作曲与编曲,集创作、演唱和演奏于一身。
在蒙古族传统音乐中汲取养分的同时,安达成员们亦从当代音乐和流行文化中找寻灵感。乐队里负责托布秀尔、呼麦和图瓦三弦,且擅长编曲的乌尼,是与那日苏自小一起学习传统音乐的蒙古族青年,同时他也十分热爱摇滚乐。在他编曲的《江格尔》中,就能听到摇滚的元素和激情,与传统音乐发生的碰撞。乐队中最全能的乐手阿乌日根,不仅会演奏蒙古族的传统乐器,还擅长钢琴、吉他等,他将这些“西方”乐器也融入安达的音乐中来。

而走下舞台,许多成员仍是地道的牧民。组合主唱毕力格巴特尔,其名在蒙语中是“智慧的英雄”之意,他就是一位真正生长在草原深处的牧民、是牧区里远近闻名的长调歌手。这也是为何安达的音乐能如此动人,因为这些音乐是来自他们的草原、来自他们的生活。虽然安达“游牧”于世界各大舞台,但是他们从未真正疏离游牧根性化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
随后那日苏简单介绍了安达成员们在“表演者”之余、作为“老师”的身份,主要是引进到内蒙古艺术学院之后的工作,尤其是与杨玉成(博特乐图)教授及其学术团队的合作。可以说在安达成员身上,当代民族器乐表演者的多重主体性彰显无遗。
二、其器·民族器乐的当代性
工作坊的第二个部分,那日苏和安达成员为大家介绍和展示了他们的乐器,让我们看到安达组合如何让手中乐器在表现草原意象的同时,通过创造性的改良与运用,找到属于安达自己的声音。如何在传统与当代不同的声音审美中,融合自有与外来,勾连传统与当代。
马头琴可以称得上是蒙古族音乐文化的象征,那日苏告诉我们,传统马头琴是用兽皮蒙面,但现代改制之后,通常用木板取代兽皮,类似西方的大提琴。但与之不同的是,许多蒙古族乐队都有自己独特的定弦,安达所用的马头琴定弦是C-F,是根据乐队的嗓音、曲目、音域和需求定的。那日苏提出,如果马头琴像大提琴一样统一定弦,可能会让这件乐器失去许多魅力。
低音马头琴的诞生是传统与当代融合的典型。青格乐图介绍到,在上个世纪40年代之前,蒙古国的民族乐团中都是采用的低音提琴,但蒙古国的音乐家们认为乐团还是执着于类似马头琴的、两根弦的乐器,于是就把低音提琴的四弦改为两弦,定弦采用降B-F的五度定弦。低音马头琴既体现了传统与西方的巧妙融合,更是展现了蒙古族音乐文化强大的包容性与融合性。
对于外来乐器,安达亦有其道将之融入组合之中,以追求他们所想要的“安达”的声音。不同于马头琴的反四度定弦,来自图瓦的叶克勒,是正五度定弦。但是安达成员在演奏叶克勒时,借用了马头琴用指甲触弦的演奏方法,替代传统叶克勒用指腹按弦的演奏法。这种富有能动性的创新,在布里亚特三弦中也有所体现。这件外来且音色独特的乐器在当地通常用拨片弹奏,而安达成员乌尼在演奏布里亚特三弦时,创造性地借鉴了图瓦三弦、吉他和班卓琴的演奏法。之所以选择这件乐器,那日苏解释到,蒙古族乐器以中低音为主,乐队中也通常缺少音色比较清亮的乐器。布里亚特三弦的加入,对于乐队整体的音色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更适合为偏高音区的歌唱伴奏。这一乐器的加入更是对蒙古族浑厚低沉的音色审美偏好的一种挑战与创新。
安达对于乐器有意识的改良与应用也体现在冒顿潮尔上。冒顿是蒙古语的音译,即木头之意。潮尔又可以译为“潮儿”、“抄儿”等,有“回声”、“和声”之意。青格乐介绍到,冒顿潮尔是蒙古族的传统乐器,同时广泛存在于世界范围内的各游牧民族中,有不同的称谓,且根据不同地区生态情况,出现了芦苇、竹子等不同材料制作的冒顿潮尔,可以说它是游牧文化的象征。而他在安达组合中使用的冒顿潮尔,为了避免舟车辗转中的耗损,故而改成铜制,且根据他个人演奏习惯作了个性化的设计。随后他展示了铜、木制潮尔音色上的差异,和不同地区、不同族群对潮尔中低音的各种审美偏好。此外,他还演示了如何通过按孔和口腔的细微处理来改变音高,使得原本五声的潮尔能够轻松吹奏出半音,以适应乐队传统曲目、新创作作品等各种现代化的表演需求。
最后阿乌日根为大家介绍了安达组合使用的打击乐器。蒙古族的打击乐器并不丰富,安达常用的一个是来自蒙古国的九边萨满鼓,另一个是来自图瓦的鼓。常见的图瓦鼓都是用数片木头拼接起来的,而乌日根展示的是由图瓦恒哈图乐队的鼓手用一整根自然干枯的大树树干制作而成的。那日苏也特地提到了恒哈图乐队、尤其是他们对乐器的诸多创新想法,对于安达、对于中国少数民族乐队的深远影响。

三、其乐·从传统音乐到“世界音乐”
介绍完安达其人、其器之后,那日苏讲述了安达“其乐”如何“成其乐”的故事。他回顾了组合成员们学习、成长和组成乐队的历程。从艺校学习、到进入歌舞团工作,成员们一起拉马头琴、一起学习呼麦。那日苏分享到,前期的演出更多是歌舞团性质的表演,而非一个成熟的组合。在他心中安达真正成为一个组合,是始于2007年首次赴美国巡演,他们才开始真正开始寻找“自己”。他认为组乐队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组合需要时间慢慢磨合、需要有属于自己的声音。
接下来,那日苏以“走出去——交流、展演和传播”为题,介绍了安达组合进入国际视野、尤其是走入“世界音乐”市场的经历。他们到过30余个国家进行巡演和工作坊,与世界顶尖的唱片制作团队合作,他们的音乐在世界各地获得了诸多重要奖项。此外,他们大胆尝试跨界合作,与金星舞团合作舞台剧《不同的孤独》等。
最后一部分,那日苏以“回归——创新、传承与发展”为题介绍了安达组合在内蒙古艺术学院所做的工作,包括“蒙古族呼麦艺术人才培养项目”、于2016年组建的内蒙古艺术学院民族音乐创新班——“安达班”、以及2017年成立的“安达民族音乐传承创新与传播中心”。
从这些故事中我们看到,地方歌舞团的演员们是如何转型为现代形式的乐队组合,他们如何将蒙古族音乐带入到世界音乐的叙事中,又如何作用于学院高墙之内民族音乐的创新教学与应用。正如杨玉成教授所说,安达是“下得了牧区,进得了市场,走得出国际”的团队。时代的转型、与“作乐”语境的变迁,让安达在不同观众面前、在不同语境中不断地寻找自己、不断重新自我定义。挖掘传统的同时,与当代文化潮流接轨,创造性地将“传统”和“当代”融合成安达自己的声音与叙事。安达组合通过其人、其器、其乐,向世界讲述了一个关于草原、关于蒙古族、关于安达的故事。
工作坊最后,其其格玛代表安达团队和内蒙古艺术学院,为萧梅教授颁发了“安达民族音乐传承创新与传播中心”艺术委员会委员聘书,并献上了对蒙古族人而言神圣的哈达。时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林在勇先生也到场与安达组合的音乐家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并对安达组合和“民族器乐的传统与当代演释”课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如同萧梅教授所说,安达的音乐是天边的大草原孕育出来的,从那遥远的地方发出来的声音,才能如此深地撼动我们的心灵。安达组合从传统音乐中走来,通过对蒙古族音乐深厚且独到的理解与创造,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一种文化现象。课后,在安达带给我们的感动之余,同学们就安达组合到底是传统的、还是当代的展开了讨论。在民族器乐的范畴中,如何界定传统和当代?如何融合传统与当代?表演者在其间又扮演了什么角色?这是安达带给我们的启示与思考。

【参考文献】
博特乐图:“从安达组合看民族音乐‘走出去’”,《人民音乐》,2018年,第9期。
李佳音:“从‘一个人的孤单’到现场‘一群人的狂欢’——评‘安达组合专场音乐会’”,《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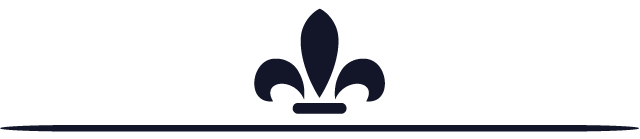
文字:凌嘉穗
摄影:刘桂腾、张珊
编辑:熊曼谕
主办:
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
协办:
香港蓬瀛道教音乐研究基金
项目资助:
国家“双一流”高校建设项目经费资助
上海高水平地方高校建设扶持项目经费资助
(萧梅教授团队“生态音乐学研究”建设项目)
往期回顾:
【工作坊综述】再现之外——谈琵琶专辑《摆》与《蓝·掉》的创作历程
【工作坊综述】“一意孤行”的中国当代音乐隐士:由《山歌》《第二中阮协奏曲》《第三交响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