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第一天同学们鲜活的田野经历分享,老师们建设性的点评,及下午海陆丰田野工作坊的精彩之后,第二天的议程同样高潮不断。活动分发言和圆桌讨论两个部分,其中个人报告分为三组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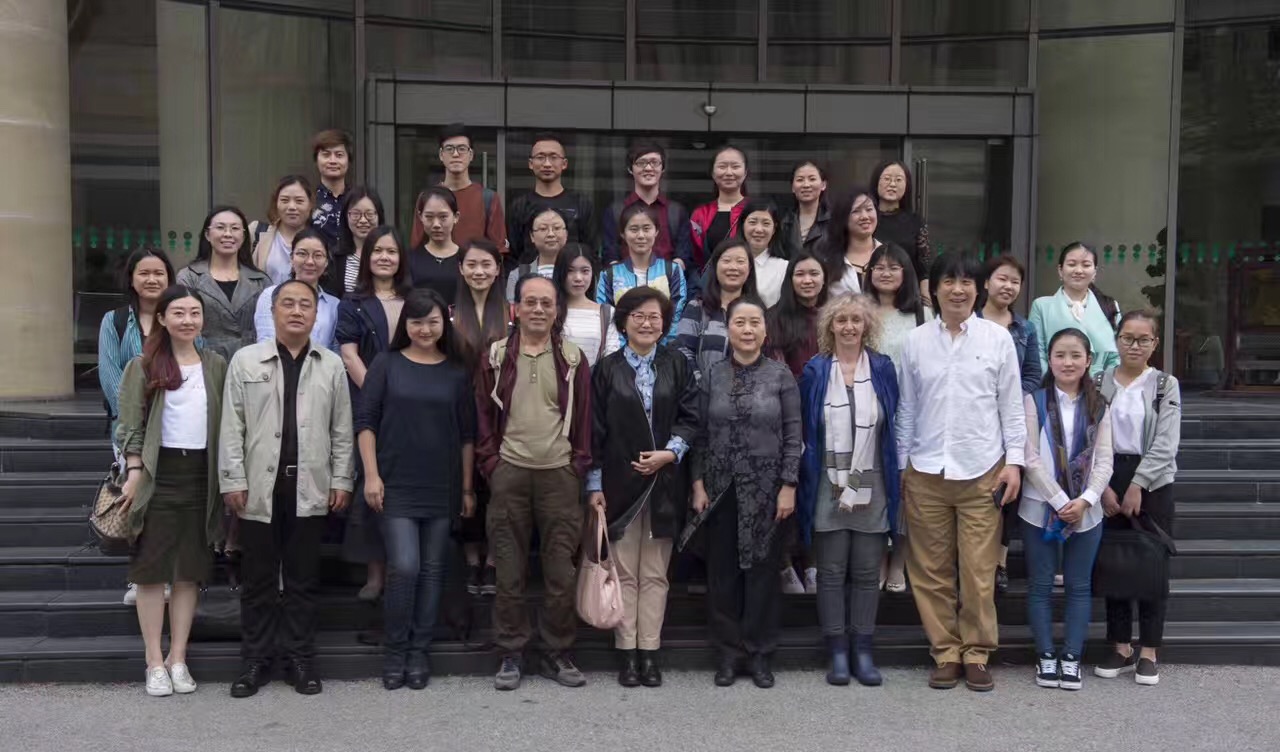
(摄影:刘桂腾、龚道远、闫旭)
一、“从北至南:从个人研究到村庄研究”
第一个单元的发言由内蒙古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包青青同学和上海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尹翔同学两篇报告组成,刘桂腾老师担任评议。


两位同学一北一南的田野点在地域分布上形成鲜明对比,两人的研究也分别面向“个人”与“村庄”,但在进入田野的过程中却同样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包青青同学的陈述分为两个要点,其一是如何从被研究对象拒绝,到开始学习;其二是如何“通过记谱”进行研究。从记谱实践开始,她发现长调“诺古拉”的演唱技法与蒙语中的“额格希格”(元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通过对莫德格老师演唱文本的分析,她就莫老师自己,以及其他蒙古族歌唱家和她自己的田野观察,在“自表述”、“他表述”、“我表述”三者之间对话,不断进行追问、反思与探讨。尹翔同学以她在海陆丰地区对一个村庄的竹马戏近2个月的考察,与大家分享她对研究者身份与视角的思考。她再次体会到,田野时间的长短及深入与否,将影响考察者对田野对象的认识。同时,在田野中,不要将视线过于集中在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是要观照与他们相关的一切事项,“田野关系”十分重要。此外,她还对“研究者的参与程度”提出反思,她认为“尽管干扰不可避免,但还是应该尽可能给予文化持有人主动权。”最后,她还强调了建立学者与田野对象良性互动的重要性,研究者不是资料索取者,应该给予田野对象适时的帮助与反馈。


通过两位同学的发言,老师们和现场的听众对“如何被田野对象”接受的这一过程,发表了自己看法。评议人刘桂腾老师提出在田野中存在很多共性问题,包括“参与-观察”这一核心问题。他借用保罗·拉比诺的话,指出“参与、观察是一对矛盾的词汇,它们之间的张力界定了人类学的空间。参与之后会产生新的观察,新的观察方法将指引新的方向去参与。”同时,“无论一个人在参与的方向走多远,他依然是一个局外人和观察者。”南鸿雁老师提出可从族群内部的身份认同出发,去理解研究对象,同时对包青青比较蒙语书写音、口语音、演唱音之间的不同,肯定了这种细致做法的价值和意义。程之伊认为在田野中,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沟通,如何相处,是一个意识问题。萧梅老师以自身在田野的发现,讲述了“搓元音”对长调“诺古拉”风格形成的重要性,提出针对音乐形态与发声方法之间的关系,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挖掘研究。她认为包青青的发言是典型的“写文化”:对不同的观点和表述的理解与阐释,如同“在他者间的迂回”。而每一次的记谱体验,亦会形成一个被认同的核心问题。杨晓老师在感叹田野类型多样性的同时,提到研究中的各种层次关系。她呼应萧老师的发言,认为青青的报告在追问、体验和认知这三者之间恰好可以用萧老师曾提出的一个观念,即“摆渡”。在记谱与口传之间“摆渡”,在自我与他者,主动和被动之间“摆渡”。对尹翔的发言所涉及到的问题,杨晓老师指出面对不同的田野,学者要转换不同的身份,把田野概念扩大,要注重当地人、政府、研究者自己、艺术团体、学校音乐教育这五种力量所形成的角力场。
二、“漂洋过海”:海外与跨界民族志
来自广西民族大学艺术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杜浩和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李纬霖分享了各自所做的东南亚海外民族志的田野,该场由萧梅老师担任评议。




杜浩同学以泰国东北部的马哈沙拉坎大学的音乐教学模式为个案,从田野的实际困难与调查成果展示两个方面发言。在田野的实际困难部分,他给出了一些解决方案,同时特别强调了田野中的安全问题,包括如何应对当地盛行的巫术。此外,他还详细介绍了泰国的传统民族音乐教学模式,提出在研究时要兼顾当地社会背景。而李纬霖同学充满激情、幽默的宣讲方式,淡化了田野的艰辛。他以傣族赞哈演唱模式为研究线索,分享了泰国、老挝、缅甸多点民族志的考察过程。他提到田野中语言、住宿、饮食等问题,而语言是多点民族志最需要克服的障碍,提出了自己学习语言时的困惑。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在关系网中获取相关信息,这是他田野工作的技巧与经验。李纬霖同学在发言结束时,还客串了一次“赞哈”,与大家一起进行了“场景再现”式的互动。


萧梅老师指出海外民族志相对来说会更加艰辛与不易。并对杜浩报告中“高校的传统音乐教育层面的考察不能忽视社会背景的影响”的具体细节提问。并认为学习不同民族语言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在学习他者语言的过程中,也可以加强对汉语的理解。Gisa Jähnichen老师建议杜浩同学要更进一步区别音乐中的传统与流行因素。来自新疆的博士研究生王倩认为巫术宗教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去认识。李纬霖同学就杨晓老师提出的“该怎么看待赞哈演唱模式”这一问题回应道,“模式”是局外人强加的观念,演唱者内心也会有一个模式,不同的歌者的模式不同。刘桂腾老师则提出多点研究与普查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来自西南的声音
第三个单元发言的同学分别是来自西南民族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李静和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朱腾蛟,杨晓老师担任点评。




李静同学分享了羌族��儒节仪式的调查与体会,并围绕这个传统的祭祀神灵、祈祷风雨的仪式活动,展示了仪式中不同环节的田野图像与视频。与大多同学一样,她也在田野中面临着语言不通的难点。此外,她也提出了面对大型仪式,个人而非团队在拍摄仪式活动的难度问题。她针对具体的研究,提出“音声”这一概念到底该如何理解。朱腾蛟同学回顾了自己从本科、硕士直到目前的博士阶段的田野经历,分享了自己在西南少数民族民间歌唱调查与研究的体会与思考。与惯常的个案研究不同,他的田野是区域性的。因此,跨地点、跨文化的“多点”田野在语言的学习、记谱、歌唱实践、田野伦理等层面均给研究者带来许多的挑战。针对这些困难,他分享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发言聚焦于壮族歌唱表演风格,并以自己在田野观察和歌唱实践为例,提出对壮族“双人搭档”歌唱形式的思考。最后,他也以自己在田野中对假声歌唱的学习为例,为在场的师生们高歌一曲。


针对两位同学的报告,各位老师发表了各自的观点。评议人杨晓老师就李静同学发言中的田野方法及“重构的传统”,提出要进一步聚焦与定位研究方向。刘红老师对仪式研究中术语翻译的转述会不会失去原有文化涵义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针对李静同学的提问,刘老师认为对音声的理解,需要结合具体行为与局内人的生活状态去把握,并学会把田野作业与写文案的工作分开对待。萧梅老师认为在陈述中要把握好立场,针对传统的建构问题,需要充分展示出局内人的目的与诉求。刘桂腾老师进一步针对朱腾蛟同学和李纬霖同学发言中提到的“多点研究”内涵,提出疑问。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多点”和“普查”,或“多点”与“比较”?此“多点”与人类学领域提出的针对同一事件的链环式追踪的“多点民族志”有哪些不同?此“多点”是一个现象问题,还是“方法论”问题?李纬霖同学则回应道,他所提出的多点,更多的具有“线索民族志”的意义。
四、圆桌讨论:田野就在你与我之间
下午的圆桌讨论会由刘红老师主持,讨论内容主要针对论坛中同学的发言、海陆丰田野工作坊,以及同学们在平日学习中的困惑、感受等进行分享与提问。为了更清楚的呈现讨论内容,本文将参与者的发言以记录形式展现。

刘红:又到了圆桌讨论的时间,希望大家打破界限,就整个论坛本身,老师同学们有怎样的想法,甚至超出这个会议之外的内容,都可以共同来探讨。我相信这样的活动越多,尤其是我们的身心状态参与得越多,我们的田野会做得更顺畅,田野之后做出来的文章也更加漂亮。这两天,老师们说的比较多,我们的讨论,希望以同学们为先。
田薇:昨天听了几位同学对土家族的报告后,我想就如何处理局内人和局外人关系这一问题跟大家来探讨。对于河北高碑店的研究来说我是一个局外人,但相对于土家族的丧葬仪式和刘老师团队研究的哭嫁歌而言我是一个局内人。昨天张春蕾同学讲土家族葬礼有5个昼夜的香火不断,为此她提出了是否人性化的问题。但葬礼在我们家乡是非常被重视的,5天的仪程在我们家乡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还有更多。但局外人就有点不适应。
李纬霖:我跟你有过相类似的经验。我是西双版纳的哈尼族,相对外面的人,我可能算局内人,但是对赞哈歌手来说,我又是一个局外人。所以局内局外在很多时候不是绝对的,在做田野工作的过程中要时刻转换自己的身份。我拜完师之后,大家并没有叫我赞哈,我也没有真正的成为局内人。随着田野的深入,当我们分析问题的时候还得再跳出来,研究过程中需要不断的融入和跳出,才能处理好这个关系。
刘红:局内局外的关系我曾在公开的场合及相关的文章中提到过。其实对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做清楚、说清楚,然后把不懂的,想弄懂的表述清楚,这样局内局外的身份自然而然就比较清晰了。这些概念是在理论方法层面上提醒大家应该注意什么问题。第二,张春蕾同学提出的葬礼习俗不人性,是因为我们在用当代的节奏看传统文化而产生的观念冲突,但我们是否要尊重这个习俗,尊重这种文化呢?
刘琳(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各位老师好。我现在做的论文和辽代的佛教音乐有关,我的资料中有一套辽代佛曲,接下来打算进一步对这个资料进行挖掘。
刘红:那么以你的选题为例,在参加了田野论坛之后,对你最大的帮助和启示表现在哪里?
刘琳:我对仪式和音乐之间的关系更清楚了。原来对仪式音乐的概念是混淆的,应该要把仪式形式说清楚,然后在仪式这个载体上再去说音乐,它们实际上是一体的。
刘红:你说仪式作为载体,“载体”这个词用得不是特别准确。不是说有怎样的仪式就有怎样的音乐。我们跟那些和尚、僧人接触打交道的时候,他们不会说:你说音乐啊?好,我给你表演一段音乐。但他们现在会这样理解。如果你对他说:音乐是仪式本身,他一定会告诉你:这不是。
王倩(新疆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首先,我想与大家分享自己的学习经历。接触到民族音乐学这个学科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通过人类学的学习,尤其是能够表达人类丰富情感的音乐人类学,我强烈感受到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的那种感动。我记得有一位老师分享过:通过人类学还有音乐人类学的学习,可以做一个大写的人。这句话给我特别的深感触。在学习过程中,我感觉民族音乐学这个学科非常具有包容性。我研究生时期受过一段社会语言学的训练,根据青青上午的报告,我想到完全可以用社会语言学、结构语言学的方法去分析长调的唱词。我认为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多听多看的方式,在不同的对话中找到突破口。我想跟各位探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南老师说的人文关怀的问题。我个人理解并不是给研究对象提两箱牛奶,送个羊腿把子什么的,解决他们的吃穿。随着社会的发展,少数民族的身份逐渐丢失,通过我们的研究也许可以帮助他们逐渐找到自己的民族身份,或者是一种回归。第二个问题是田野作为研究的手段在我们的研究中占了多大的比重和篇幅?理论又占了多大的篇幅?我现在比较焦虑语言的问题,我现在在学维吾尔语,但学到的是官话体系,这对实际的田野是否有帮助?
刘红:人文关怀的问题,要提到语境(context)这个词,需要在不同的语境中去看待这个问题。人文关怀在具体情况下有不同的对待方法,以不同的方式而存在。第二,关于理论跟田野之间的关系,它们二者也不是截然分开的。我们研究中的理论阐释或相关学术观点的提出,有一部分是基于田野形成的。而纯粹的理论研究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
云南大学艺术学院学生:我有两个问题。在昨天哭嫁歌的案例中,提到了“一场被安排的调研”,我之前也有这样一次经历。不同的团队在不同的时间去考察同一个对象,但接待的人员、联络人,还有歌手都是一样的。这给我们调研带来一定的便利,但这些音乐有可能并不是我们想要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安排的人也在保护音乐,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传统音乐的传承,。第二个是“再研究”(restudy)的问题,昨天老师们对这个概念有所讨论。我在调查畲族民歌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微信对歌。现在歌圩不存在了,特别喜欢对歌的一些阿姨,就用微信对歌。结合刘老师团队讲的内容,“再研究”是否可以理解为对同一对象在不同的时间、空间里的一些新研究?
刘红:受限于研究生的学制,在三年之内,学生们要修课、作业、做田野、写论文,要在这么短时间做这么多的工作,学生是非常辛苦的,但他们都做到了。“被安排好了的调研”,这个情况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当你在田野考察时,住到某个村子里后,他们今天安排,明天安排,后天又安排,一个月的安排,但我不相信他们一年都会为你安排。所以你住进这个村子以后,一切就像淘金子淘得干干净净。这种做法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明知道自己的时间仓促,那么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做一些可以做的工作,但这类情况可以避免。这需要时间,需要调查者能够深扎下去。但对缺乏时间学生来说,有些勉为其难。第二关于“再研究”(restudy)是在理论层面建立我们工作的一个构想,我们怎么去做研究的一个模式。“再研究”不是从理论上去讨论深究的一个问题。我们要活学活用,根据不同的事实,区别看待相关理论。就如刚才说的局内人,局外人,这些都是我们在学科学习过程中必然要接触到的概念。理论研究是就理论本身的研究,有点类似我们说的哲学层面,那是理论家做的,但我们是在理论指导之下做具体的研究,所以不用在这些概念上有过多的纠结。
闫旭(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我想分享两点感受。会议前两天我刚从田野回来,我和刘桂腾老师及师妹尹翔去南通看了一个童子会的仪式,结合这两天的活动,给我感触最深的是:仪式、音声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对我来说不是书本上的那个概念,它变得更加的有血有肉。仪式发生的时候,有一种场的力量会让你去信这个仪式。我们在南通时,有位会首的老奶奶拉着我的手问我:你们信我们这个东西吗?当时我和师妹一时语塞,因为我们还没有见过这个仪式,谈不上是信还是不信。当时刘老师回答:如果我们不信我们就不会来了。这句话的道理是很深刻的,因为仪式它具有这种力量。刘老师身经百战,他是有这种经验的,但是对当下的我们来说没有那样深刻的认识。我们的这种信和局内人的信并不在同一个层面。对我们来说,无论持怎样一个观点,不管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者,一旦我们进入那个场域,仪式本身就带有那种感染力。就像哭嫁歌的仪式,我们即便没有亲临现场,但听她们的讲述也很有触动。一个仪式的存在有它存在的意义和力量。第二是关于海陆丰的田野。昨天杨晓老师引用萧老师话:田野它会开出一朵花来。海陆丰的田野对我来说,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更加清楚的认识自己。进入海陆丰之前,我对这个地方怀着揣测和先验的认知。可当我真正进入这个田野时,便发现自己特别的无知、浅薄。通过昨天的工作坊大家可以看出,所有的老师都身怀绝技,三位老师之前都没有合作过,但是他们仅凭借各自对曲目的了解,相互之间可以配合得非常好。郑俊锦老师他既会打鼓,又会吹唢呐,也会拉大广弦,而且他的大广弦是自己制作的。他在自己一次演戏的经历中,发现戏台旁边有一棵长得非常好的龙舌兰,他就去挖了来,然后回去做成了这件乐器。艺人们一个个就像活字典一样,听到任何东西,能立马讲出许多见解。每一位民间艺人都非常了不起。反照我们自己,从小音乐培养直到进入专业院校,接受这么多的音乐教育,在一些情况下,我们与民间距离是非常遥远的,我觉得有很多东西要向他们学习。
刘红:很好,充分的表明了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尊重。
包青青:大家的研究,有很多是对“他文化”的探讨。语言不通会给研究者带来一些困扰,在有些情况下不能明白研究对象想要表述出的问题。很多去内蒙的人看我们蒙古族的音乐表演,会问我一些音乐术语用汉语翻译是什么意思。虽然我清楚它们在蒙语中的涵义,但用汉语表述会担心对应有误。我们研究“他文化”时,对“他者”的表述非得要用“我们”的语言去翻译吗?蒙语中“额格希格”不仅仅是元音,而翻译成元音后导致研究者做分析时往往会忽略辅音。这不是翻译存在的问题,而是我们可以去解释、阐释这个术语本身,并不是把“额格希格”对应成汉语的“元音”。我们在转述的过程中,要认识音乐术语的文化体系,这是我这两天的最大收获之一。
董岚清(浙江音乐学院本科生):哭嫁歌小组“小动作引发大问题”的发言中提到的一些细节是我之前没有注意到的。虽然小动作确实是能隐伏一些大问题,但是小动作同时也具有一定偶然性,大内容也具有自己的主观性,我想请教各位老师,怎么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刘红:这是一个相对观念。我们的这个作业,并不是要去解释每个相关小动作,而是提醒学生在做口述史时,对口述资料的真假,准确性,要保持警觉,并辨别。这是一个觉悟意识,不是实际操作要做的。细节的问题很重要,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打引号的“身经百战”的资料提供者。
孙作东(东北师范大学在读博士):我的论文是做满族民歌的歌唱风格与其传统研究。满族民歌的存在方式主要有三类,一是用满语演唱的满族民歌;还有用满族音乐元素创作的新满族民歌,也就是展演中的满族民歌;活态的满族民歌现难以找到。那么我找的这些资料能不能代表以后的满族民歌?面对这样的现状我要如何深入去做这个研究?
刘桂腾:现在不能说拿出一个方案,我们只能讨论。就像刘红老师说的,你把一个个案讲清楚了,描述清楚了就可以。“代表性”的问题,类似青青报告中提到莫德格老师演唱的长调能不能代表乌珠穆沁的长调风格的追问。
刘红:有两个关键的基本前提要明确,你做的研究属于什么性质。是对活存现象的研究,还是曾经存活在某一个状态里面,而现在已经没有了。如果是综合性的研究要考虑具体落实到怎样的人和怎样的环境。如果仅仅是在纸面上研究这个问题,那么严格按照做纸面文章的规则去做。做田野不是找例子来证实自己对某些现象的看法是否正确,如果连一个(传承)人都找不到就不是一个活存现态的研究,可能变成了一个普查性的研究,或者是概括性的研究。
刘桂腾:这涉及民歌风格和传承两个问题。研究对象有以纸面为载体的,还有发现的活态的满族民歌,作品性质的满族民歌。现在东北有很多人在尝试创作满族民歌,在一定条件下这也是一种传承方式,就像黄翔鹏先生说川江号子,是音乐会式的传承。现在已经没有那种劳动生活了,因此它只能在舞台上呈现。活态传承的生存现状比较差。
萧梅:满族民歌是个很大的概念。研究选取的时间点和空间点很重要。要发现问题就要去做调查,在调查中才能知道能做什么,根据田野资料决定可以聚焦的问题。风格研究需要有一个活态的东西。
李静:在田野中,研究者会被仪式的信仰力量感染。这种感性会不会影响论文呈现?
刘红:不会。首先,不要用理论框住自己。当你看到仪式中的一些行为,比如宰杀牛羊,你要相信这些牺牲的牛羊就是神牛和神羊,这时用宗教语言学中表征性的语言,对他们所做的表述清楚,而不要加入自己的想法,去表明态度。第二,瞄准你所要讲述的对象,用象征性语言做解释。
南鸿雁:同学们在做研究的时候,要以田野论田野。我比较欣赏学生们能坦率分享自己在田野中发生的事情和思考。
刘桂腾:我要强调田野技术层面的规范性问题。从同学们的报告来看,其中有70%的影像文本是不合格的。提高这些基础技术有利于你们的学术表达。
不知不觉,既定的圆桌讨论时间已近尾声,参与者却意犹未尽。主持人刘红老师请萧梅教授作总结发言。
萧老师感慨到:非常感谢这次参与论坛的同学和老师,给予我们那么多不同的案例和思考。我突然想到第一次给杨晓上课的时候,是在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那时讲的就是实地考察。一晃经年,学生们已经过去多少代了,我有种长江逝水之感。大家的发言从自己遇到、思考的问题,无论是学术、田野到你们自己,都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以前,在外面的那个年代,不可想象学生们的头脑中已装了那么多的方法理论。此外,我们那个年代也没有那么多人身安全的问题(笑:恐怕拉肚子是最大的问题)。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讨论的话题也在变。举办这个论坛,对我个人而言真是教学相长。大家带来那么多鲜活的田野案例,你们讲述的田野体验,让我们学到很多。就我们这个领域来说,田野是非常重要的基石,田野决定我们能提出什么问题,你的研究能做到的深度和广度就取决于你做的田野。
杨晓刚才希望我能就女性学者的田野谈一谈,我觉得可以分两个层次。第一是从学生如何通过做一篇学位论文,在过程中接受某种历练,学习怎么与人相处。因为这个学科所谓的实地考察,最根本的学习就是如何跟人打交道,并学会换位思考。这是学生在做论文过程中得到的收获,尽管毕业后可能并不最终选择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为自己从事的职业。而另一个层次,是你选择读了博士,选择了以这个专业为生。那么就需要去平衡。在现实的基础上,平衡在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我总是喜欢跟我自己的学生说,研究是一辈子的事,田野是一辈子的事。而作为女性,做田野有她的难处,但也有特别的优势。(孔注:现场有人插话:女生更细腻。萧老师回答:呵呵,是的,女生更细腻,但也不尽然,我自己就是一个“马大哈”。)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但女生做田野,相对来说融入比较容易些。但女生尤其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亲疏远近,要敏感,防范于未然,防止陷于尴尬之境。但遇到问题也不要怕。
总而言之,“田野”始终是我们呼吸的重要方式。就我个人而言,我在田野中感到最幸福的是你在某种程度被“解构”,这可能是认知上的,也可能是情感上的。如果长期禁锢在某种思想中,人就会固执,而到田野中就是从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这个时候就可以重新焕发你对生命的热爱与思考。另外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不要背包袱,许多问题其实是一个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就是田野对我们的滋养。我总是喜欢说,田野是能自行向你打开的一本书。每一次与田野对象结识的缘分是求不来的,我们获得的远远比失去的要多得多,获得更多未知的体验和更多人生的滋养,这才是最重要的。理论是灰色的,但生命之树常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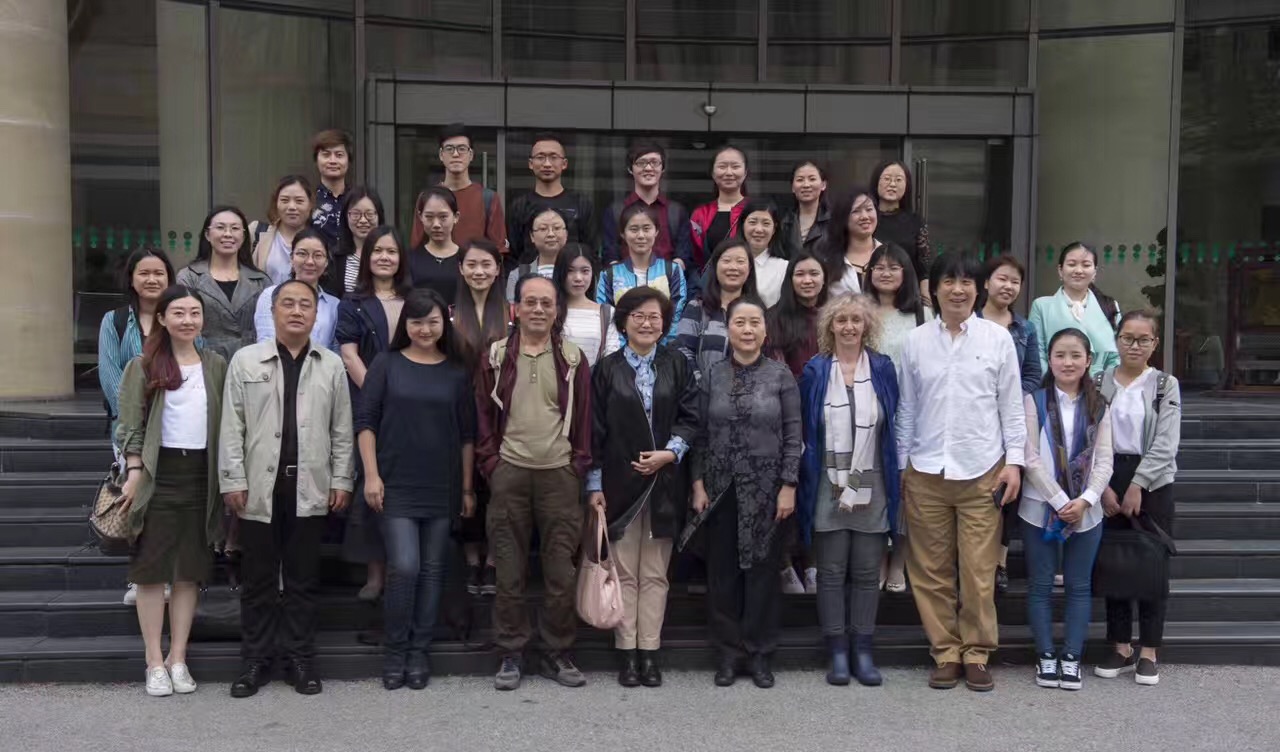
主办单位: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
上海高峰高原学科建设项目·艺术学理论·中国音乐生态学团队
协办单位:香港蓬瀛道教音乐研究基金
(摄影:刘桂腾、龚道远、闫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