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年 12月12日 9:00—11:30
地点:上海音乐学院教学楼贵宾室
综述人:朱腾蛟
第八届“大音讲堂”之圆桌会议于2015年 12月12日上午上海音乐学院教学楼贵宾室举行,参会人员包括:约翰·贝利(John Baily,英国民族音乐学家)、萧梅(主办方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主任)、李海伦(Helen Rees,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刘桂腾(沈阳音乐学院硕士生导师)、黄凌飞(云南艺术学院教授)、徐欣(中国音乐学院教师)、魏育鲲(扬州大学教师)、苏毅苗(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谭智(大理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宁颖(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后)、李亚(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朱腾蛟(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以及其他来自上海音乐学院、云南艺术学院等高校的博士、硕士及本科生等。
圆桌会议主要围绕贝利教授的讲座与民族志电影内容展开交流,引发了学者们关于音乐与身体等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与讨论。会议由刘红教授主持。

(刘红教授主持圆桌会议)
首先,萧梅教授代表主办方发言。萧梅指出贝利教授的讲座与民族志电影两个部分正好形成一个呼应或者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连环。一般而言,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不是就音乐作品而论的,而是把对音乐“结果”的关注转向对音乐“过程”的关注中。如果把阿富汗音乐置于中间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贝利教授的研究正好形成了两段“过程”:其一是音乐的“生成过程”(generating);其二是音乐的“社会化过程”。这两个“过程”便形成了整个音乐文化的内核,这也正是民族音乐学审视“何为音乐”与“如何研究音乐”的重点。就“过程”研究而言,学科在一段时间以来对学科方法与理论的讨论中比较重视音乐的“社会化过程”。尽管就音乐“生成过程”的研究在西方学界已有梅里亚姆(Alan Merriam)、约翰·布莱金(John Blacking)等前辈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在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发展中对于这一部分的研究是不够透彻的,这与我们对身体在音乐研究中的认识不足相关。尤其是我们长期以来受制于西方“谱系统”的背景下,往往身体的研究在学科中只是辅助手段,没有把身体作为与音乐直接相关的部分进行研究。但是,中国传统音乐的特点恰恰是以表演者的演奏为中心的,而不是以作曲家的作品为中心。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如何以演奏家为中心的问题,身体是不可忽略的中心点。

(萧梅教授发言)
刘红老师进一步谈到中国传统音乐中“体认”与交流并不比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少,身体与音乐的关系更为直接。在我们的许多习语中都有所体现,比如我们常说传统文化都是“口传心授”,但事实上这其中必不可少的包含着“口传身授”的观念,传统音乐在传承中乐师都是身体力行的。
作为回应,贝利教授指出研究者在研究中所面对是一个“思考的身体”,不仅大脑在思考,身体也在思考。在学习表演的过程时,起初我们需要专注,但在随后就逐渐成为了一种“例行的行为”(routine act)。在西方音乐文化中,经历过这样一种学习过程的表演者,反而会忽视它,这一直是他反对西方音乐学家研究的原因,因为在他们的研究中身体被忽视了。他们认为身体只是音乐发展所需要的“低级工具”,并认为西方音乐中最高级的行为是属于作曲家的,而作曲家不需要用身体进行创作,只需要运用头脑,在头脑中听到的声音,然后被写到了纸上,所以身体在创作中就不复存在了。

(John Baily教授发言)
刘桂腾老师围绕贝利教授在放映民族志电影前谈及的对于讲述事件型(tell)与展示事件型(show)两种民族志电影类型的选择进行发问。贝利从自己的学习经历谈起,解释了“观察式的电影”(observational cinema)“田野考察式的电影”(fieldwork movie)两种类型的区别与关系,并对其民族志电影作进一步解释与信息补充。

(刘桂腾教授发言)
接下来,参会者们围绕身体、表演与情感的互动关系、文化交流与身体感、器乐与声乐表演中的身体研究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李海伦教授发言)
最后,会议在大家意犹未尽的讨论和学术的热情当中拉下帷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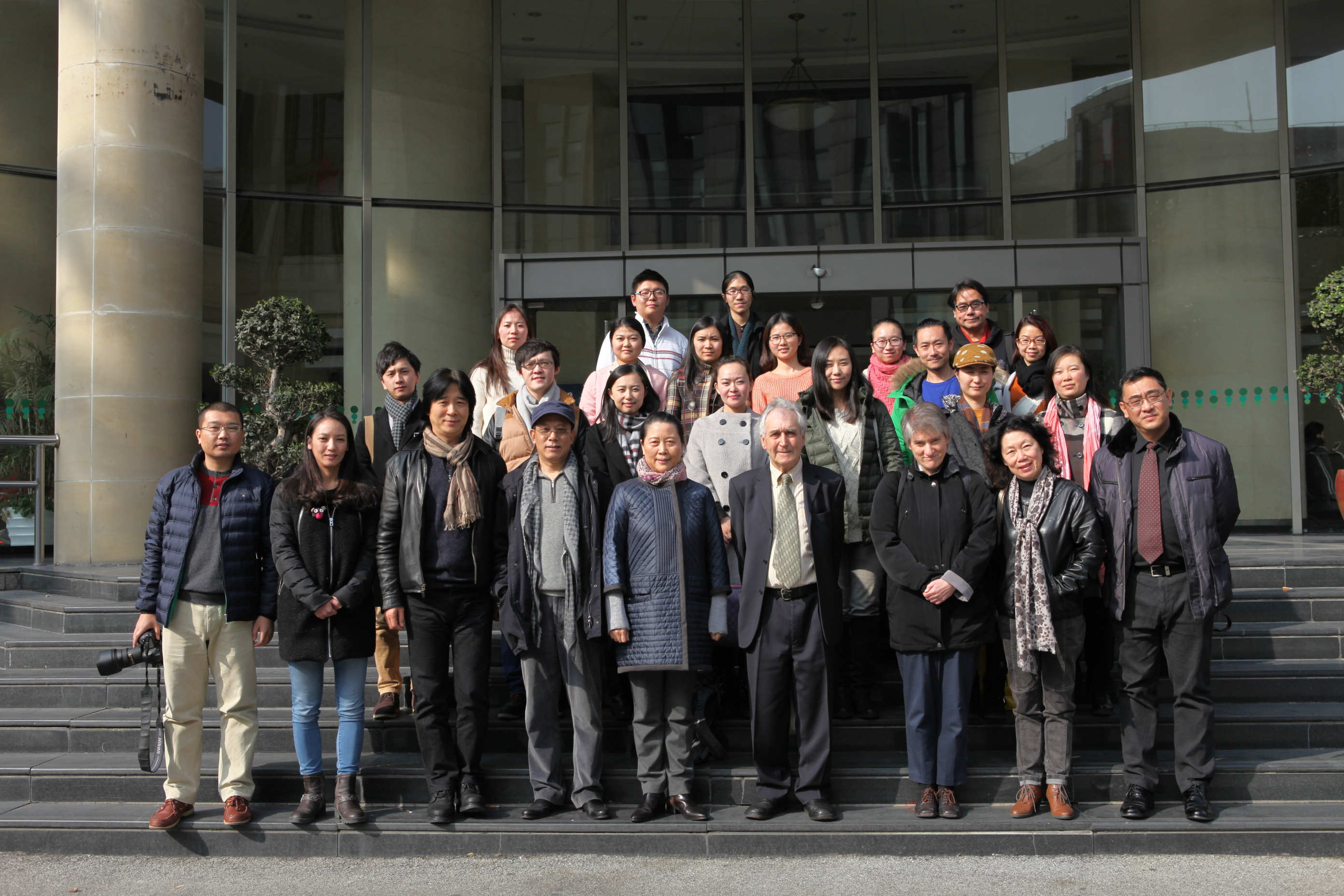
(第八届大音讲堂参会成员合影)


